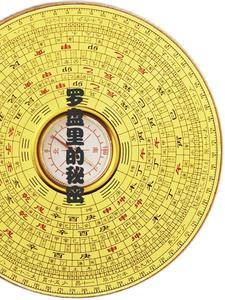02小说网>熵光夜城 > 第188章 人类触光 指尖上的第一次黎明(第1页)
第188章 人类触光 指尖上的第一次黎明(第1页)
那一声撕裂世界的裂帛之音终于消散了,连同那长达一个世纪的轰鸣与战火,一同归于虚无。整个地下城还沉浸在巨大的、令人晕眩的耳鸣之中,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所有的目光——无论是人类那浑浊充血的眼睛、义眼冰冷精密的光学镜头,还是机械士兵那正在疯狂对焦的传感器——此刻都死死地钉在了头顶那道刚刚被暴力撕开的、狰狞的伤口上。起初,那里只有狂暴的辐射乱流,像是一道流脓的疤痕,翻滚着暗红与深紫的混沌色彩。但很快,在那混乱、肮脏的颜色背后,出现了一抹从未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颜色。那不是刺眼的白,也不是警报的红,更不是霓虹的彩。那是纯粹的、温暖的、不含任何杂质的、足以烫伤灵魂的金色。首先出现的,是一缕极其细微的光线。它从天幕裂口的最顶端,像是一根刚刚融化的金丝,试探性地、甚至有些战战兢兢地垂了下来。它穿过了那些还在裂口边缘翻涌的、带有强烈腐蚀性的蚀气云层。那些黑色的云雾像是有意识的触手,试图缠绕、吞噬这缕外来的异物,但这缕光在云层中忽明忽暗,显得那么脆弱,那么纤细,仿佛一阵来自废土的寒风就能将它吹断,或者吹灭。它在半空中摇曳,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又像是一个谨慎的神明,在确认这个充满了罪恶、杀戮与黑暗的流放之地,是否真的值得被照亮。地面上的人们屏住了呼吸。数十万人的呼吸在这一刻同时停滞,没有人敢出声,甚至没有人敢眨眼。恐惧像是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他们的心脏——他们害怕这是一场幻觉,更害怕这缕光会因为看到他们的肮脏而缩回去。仿佛听到了这来自深渊底部的无声呼唤,又仿佛是感受到了那个名为“猩红天幕”的巨神意志的牵引,那缕犹豫的金丝,突然不动了。它在半空中停顿了大约一微秒,在那一瞬间,它似乎完成了某种从“观察者”到“审判者”的身份转变。它鼓足了所有的勇气,变得坚决了一些。它开始变粗,从一根脆弱的发丝,变成了一根坚韧的绳索,又变成了一根粗壮的光柱;它开始变亮,从微弱的荧光,变成了耀眼的烈日。伴随着一声只有灵魂才能听到的共鸣,那道光终于刺破了最后的阻隔,冲散了最后一片试图阻拦的黑云。它不再犹豫,不再试探,它像是一柄被神明遗落在人间的圣剑,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带着积蓄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动能,笔直地、毫无保留地、轰轰烈烈地插了下来。当那道直径超过百米的光柱真正接触地面的那一瞬间,没有预想中的毁灭性爆炸,没有冲击波掀翻建筑。只有一种极其轻柔、却又无法忽视的、密集得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叮……叮……咔嚓……叮咚……”那是热胀冷缩的声音。废墟中,那些沉睡了一百年的金属残骸——断裂的工字钢、扭曲的车辆底盘、生锈的管道——在接触到真实阳光温度的瞬间,发生了微小的物理形变。冷缩的金属分子在光子的撞击下迅速活跃、膨胀。生锈的钢筋在舒展它的筋骨,发出了清脆的崩裂声;变形的铁板在恢复它的弹性,发出了悦耳的弹跳声;甚至连那些坚硬的混凝土块,也在受热不均中发出了细微的噼啪声。这无数个微小的声音汇聚在一起,竟然形成了一首如同风铃般悦耳、又如同暴雨击打琴键般宏大的交响乐。那是物质在欢呼,是这片死寂了百年的大地,在光中苏醒时唱的第一首歌。光柱并不是静止的,它像是有生命一样,在地面上扩散、流动,如同金色的水银泻地。它照亮了空气,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空气中漂浮着这么多东西。那些平日里根本看不见的浮尘、孢子、微小的金属屑,在这一刻被强光捕捉。它们不再是肮脏的灰尘,在廷德尔效应的作用下,它们变成了飞舞的金粉。它们在光线中旋转、上升、下落,沿着热气流的轨迹翩翩起舞,每一粒灰尘都反射着太阳的光辉,每一粒灰尘都像是一颗微型的恒星。整个世界仿佛被加上了一层神圣的滤镜,原本破败不堪的废墟,在这些“金粉”的装饰下,竟然显现出一种庄严的、古典的废土美学。地下城的幸存者们,终于从他们藏身的洞穴、废墟缝隙、生锈的集装箱里,一点点地挪了出来。他们的动作很慢,很僵硬,像是一群刚刚结束冬眠、还带着满身泥土气息的野兽,正试探性地伸出爪子,去触碰那个陌生的新世界。在一个塌了一半的混凝土掩体后面,一个年轻的母亲正死死地抱着怀里的婴儿。她身上的衣服早已看不出颜色,满是油污和血迹,头发像枯草一样乱蓬蓬的。她不敢出去,那一束束从头顶裂口射下来的强光,对于她来说,就像是某种未知的辐射武器。但她的孩子醒了。那个只有三个月大、从未见过太阳、因为长期缺乏日照而皮肤苍白透明的婴儿,正瞪着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掩体边缘那一块跳动的光斑。那里,光线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微尘,婴儿伸出了那只瘦弱的小手,咿咿呀呀地想要去抓那些光点。,!母亲下意识地想要把孩子的手拉回来,想要用自己肮脏的衣襟遮住孩子的眼睛,她颤抖着低语,声音里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但就在她的手指触碰到那块光斑的一瞬间,她停住了。那是……什么感觉?指尖传来一阵轻微的刺痛,紧接着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酥酥麻麻的暖意。那种暖意顺着指尖流进血管,像是一股温热的水流,瞬间冲散了她骨髓里积攒了二十多年的阴冷。她愣住了,慢慢地、试探性地把手掌摊开,放在那束光里。手掌上的污垢、老茧、伤疤,在强光下纤毫毕现,但这只手,正在变热。母亲抬起头,看向怀里的孩子。阳光正好照在孩子那张皱巴巴的小脸上,孩子并没有哭,也没有躲。相反,他笑了。那是一个无意识的、纯粹的生理性微笑,因为温暖,因为舒适,因为那是生命本能的向往。母亲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她不再躲避,紧紧抱着孩子,一步步地,走进了那片金色的海洋。在人群的另一侧,站着一群如同雕塑般的守夜人。他们的动力甲已经残破不堪,上面布满了弹孔和爪痕。凯尔站在最前面,他的左臂已经断了,空荡荡的袖管在热风中摆动。他依然戴着那个全覆式的战术头盔,那个头盔的面罩上全是裂痕,滤光镜片早已模糊不清。他习惯了躲在这个铁壳子里。这不仅是为了防蚀气,更是为了防备这个世界。在这个头盔后面,他可以冷酷,可以无情,可以是一个杀人机器。但现在,他感到一阵燥热。阳光照在黑色的金属装甲上,迅速升温,头盔里的空气变得闷热难耐。身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那是金属卡扣被解开的脆响。凯尔回过头,看到一个年轻队员正在用颤抖的手,解开脖子上的气密锁扣。那年轻人的手指因为激动而显得笨拙,好几次都滑开了。“别……”凯尔本能地想要制止。这是违反守夜人条例的,在户外摘下头盔等于自杀。但那个队员已经摘下来了。一张年轻、苍白、布满汗水和油污的脸庞,暴露在了空气中。没有腐蚀,没有窒息,没有暴毙。那个年轻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仰起脸,闭上眼睛,任由阳光洒在他满是青春痘的额头上。“好暖和啊……”年轻人喃喃自语,脸上露出了一种近乎痴傻的笑容,那笑容里没有杀气,只有单纯的快乐。凯尔的手,慢慢地摸向了自己的下巴。那里有一个生锈的卡扣,因为太久没有使用,已经有些卡死了。他用力扳动了一下。“咔嗒。”一声轻响。那个沉重的、沾满血腥味和机油味的头盔,被他摘了下来,随手丢在了地上。头盔滚了几圈,发出一阵沉闷的撞击声,最终停在一块被晒热的石头旁。凯尔眯起眼睛。强光刺得他流泪,但他没有闭眼。他用那只完好的右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那张脸上有三道狰狞的伤疤,是从左眼角一直拉到嘴角的旧伤,那是五年前被一只盲眼猎手抓的。此时此刻,阳光正温柔地抚摸着这道伤疤。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替他擦去脸上的血污,抚平他内心的褶皱。“这就是……你看到的景色吗?儿子?”凯尔低声问道。他的声音沙哑、破碎,像是含着一口沙砾。他的喉结剧烈滚动,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哽咽。然后,这个一辈子没在人前流过泪的铁汉,双膝一软,跪在了滚烫的地面上。他用手捂住脸,肩膀剧烈耸动,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哭声里有悔恨,有解脱,更有迟来的父爱。在人群的边缘,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孩。她是天生的瞎子,在永夜的世界里,瞎子反而活得更久,因为他们不需要光,也更擅长听声辨位。但今天,她感到了一丝恐慌。周围太安静了,没有了风声,没有了机器的轰鸣声,甚至连人们的交谈声都消失了。“有人吗?”她怯生生地伸出手,想要摸索周围的墙壁,寻求一点安全感。但她摸空的。她的手伸进了一片虚无的温暖之中。“这是什么?”她惊慌地想要缩回手。但在那一瞬间,她的皮肤告诉了她答案。这是一种有重量的、有质感的、仿佛流动的丝绸般的触感。虽然她的眼睛看不见,但她的皮肤“看见”了。她感觉到那种热度顺着手臂向上蔓延,照亮了她黑暗的世界。在她的脑海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模糊的概念——金色。她不知道金色是什么样子,但她觉得,应该就是这种暖洋洋的、带着点甜味的感觉。她慢慢地站起来,张开双臂,像是在拥抱一个看不见的恋人。“我看见了……”她笑着流泪,那双灰白的眼珠对着太阳的方向,仿佛那里真的有一扇门为她打开,“我看见了……这是热的颜色。”不远处,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缺了半口牙的老人,正趴在地上。他用那只像枯树枝一样的手,疯狂地挖掘着地面。他挖开那一层厚厚的黑灰,露出了下面深褐色的泥土。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他抓起一把土,凑到鼻子前,贪婪地嗅着。以前,这里的土是臭的,带着尸体的腐臭,带着化学废料的酸臭。但现在,阳光把泥土里的湿气烤干了,把霉菌杀死了。这把土里,散发着一种干燥的、焦香的、令人安心的味道。那是大地的本味。老人像是个瘾君子一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股尘土味吸进肺里,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的香料。“香的……”他像个疯子一样嘿嘿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把脸埋进土里,用脸颊去蹭那些粗糙的沙砾,任由泥土弄脏他本就破烂的脸。“这是活人的土……这是活人的土啊!”风,轻轻吹过废墟,卷起了地面上残留的最后一层黑灰,在阳光下打着旋儿。远处,一块摇摇欲坠的铁皮招牌,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发出“咔嚓”一声脆响。这个声音清晰得像是炸雷。人们互相看着,看着彼此脸上那被阳光照亮的每一条皱纹,每一颗泪珠,每一块污渍。他们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同伴长这个样子。原来那个总是凶神恶煞的胖子,哭起来像个委屈的孩子;原来那个总是冷冰冰的女杀手,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原来那个总是沉默寡言的技工,眼睛里竟然藏着星星。这种沉默持续了很久,直到一声无法压抑的尖叫打破了寂静。“啊————————!!!”那是一个失去了所有亲人的男人。他跪在地上,对着天空,发出了野兽般的咆哮。那是积压了一百年的委屈,那是对逝去亲人的告慰,那是对这个操蛋世界的控诉。这声咆哮像是一个引信,引爆了整个群体的情感核弹。哭声、笑声、叫喊声、祈祷声,在一瞬间爆发。人们瘫倒在地,互相拥抱。不管认不认识,不管以前是不是仇人。在阳光下,他们都是幸存者。一对年轻的情侣紧紧拥吻,仿佛要将彼此揉进身体里;几个孩子手拉手在废墟上奔跑,跌倒了也不觉得疼,爬起来继续追逐那些光斑;一群老人围坐在一起,用颤抖的手互相擦拭着眼泪。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混乱,也是最神圣的一场狂欢。在人群的外围,新星靠在一块断裂的水泥柱上。她没有加入狂欢,也没有流泪。她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看着那些在光中哭泣、欢笑、奔跑的人们。她的手腕上,那道曾经代表着亵渎同盟指挥官权限的纹身,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身边传来了脚步声。血瞳走了过来,她的脚步很轻,像只猫。她身上的那些变异特征已经完全消失了,红色的长发在阳光下闪着金光,那双金色的瞳孔里,倒映着整个世界。“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血瞳问。新星摇了摇头,嘴角微微上扬:“不。这只是开始。”她伸出手,接住了一片从空中飘落的、被烧成白色的灰烬,“烬生给了我们一张入场券。但能不能在这个新世界里活下去,还得看这群人自己。”血瞳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半根压扁了的香烟,叼在嘴里。“借个火?”新星看了一眼天空中那轮耀眼的太阳,又看了一眼血瞳。“用那个吧。”她指了指天空。血瞳愣了一下,然后真的抬起头,拿着烟对着太阳的方向比划了一下。当然,烟没点着。但她还是深吸了一口,仿佛真的吸进了一口阳光的味道。“真他妈的……够劲。”她吐出了一口看不见的烟圈,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温柔。太阳渐渐西斜,光线从刺眼的白色,变成了温暖的橘红色。人们开始慢慢平静下来。虽然依然有人舍不得回到阴影里,但大多数人已经开始适应了这种新的环境。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摇摇晃晃地走到了一块平整的石板前。石板上,因为长时间的暴晒,积聚了不少热量。孩子伸出那只胖乎乎、脏兮兮的小手,按在了石板上。“啪。”他感觉到了石头里传来的温热。他感觉到了自己手腕上那细微的跳动。那是脉搏。那是血液在血管里奔流的声音。而那道光,此刻正穿透他薄薄的皮肤,照亮了他手腕下那青色的血管。血液是红的。光是金的。脉搏是活的。这就是烬生用他的血肉、用他的灵魂、用他的一切换来的礼物。这一刻,希望不再是一个写在宣传单上的抽象词汇。希望就是落在皮肤上的温度,希望就是眼中看到的色彩,希望就是这千千万万双手掌上,正在有力跳动的、永不停息的生命脉搏。:()熵光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