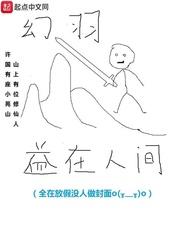02小说网>老派约会指南 > 3040(第12页)
3040(第12页)
从前寡淡无欲的面相,如今眼眶微红,上挑的桃花眼上仿佛当真沾染上上了一片桃花。他的气息不匀,胸膛急速地起伏着。
宿泱能感受到自己触碰到的心脏正在急速跳动着。
他将头靠在宿泱的肩上,嘴唇正对着她的耳朵,性感的呼吸声在她的耳里扩散,让她的心跳也跟着乱了。
宿泱抿了抿唇,这样的沈从谦少了些圣洁,多了点红尘欲气,更好看了。
沈从谦闭目闻着宿泱身上和自己同出一源的檀香,内心逐渐安宁下来。他伸手将宿泱被晚风吹在自己面上的发丝挽到耳后,指尖借此停留在这片敏感的肌肤上。
他微微戳了戳,宿泱的耳朵就红了。
红印,咬痕。沈从谦想起沈冠南脖子上那个令人心烦的牙印,他对着宿泱通红的耳垂吹了一口气问:“你为什么要咬他?”
这个他两人都心知肚明是沈冠南。宿泱不好说是沈冠南自己要求的,她笑了一下问:“怎么你也想我咬你一口吗?”
“可以。”沈从谦毫不犹豫地说。
他配合地仰头,把自己形状完美的喉结露出来,等着宿泱来临幸。等了许久也不见宿泱动作,疑惑地问:“为什么不咬?”
宿泱没想过沈从谦会同意,她心里一愣,小声骂道:“你们沈家的人是不是都有病!”
尽管如此,她还是上前一步,拉着沈从谦的领带踮起脚,寻找到他的喉结重重地咬了上去。
先是宿泱呼吸打上来的微痒,随着她的牙尖轻轻刺破皮肤,神经系统传来了痛,但沈从谦眼都不眨,只是看着宿泱。
他的小毒蛇终于亮出了獠牙。
他伸手揉了揉宿泱的头发,嗓音微哑地说:“够了。”
宿泱往后退了和他分开,她的血脉偾张,正在血管里激烈冲撞。沈从谦这样清高的人,也自愿为自己俯身,甚至甘愿露出脖颈。这是一种精神上极致的胜利,再也没有比这更爽的事了。
“我回宿舍了。”宿泱轻咳一声强装镇定地说。
沈从谦理了略微凌乱的衣转眼又恢复了他矜贵的模样,他抬腿跟上宿泱:“我送你。”
宿泱在前走,沈从谦跟在她身后。他的影子被路灯投到她的脚下,不用回头,宿泱也知道他一直在。
夜风冷清,但人心太热,越吹越热。
好不容易捱到宿舍楼底下,宿泱回头指着门说:“我进去了,你也早点回去。”
想了想她又补充道:“下次别喝这么多酒了,我不想你跑去亲其他人。”
沈从谦很认真地说:“只亲过你一个,那是我的初吻。”
宿泱有些不信,一个三十六岁的老男人怎么可能会连人都没亲过。她撇了撇嘴不再说话,只是埋头往门里走去。
“晚安。”沈从谦在她身后轻声地说。
风声把他的话语送到宿泱的心上,她回头对他挥了挥手:“祝你有个好梦。”
宿泱离开了,沈从谦还站在原地。一直悄悄跟在两人身后的王夷终于找到机会走上来问:“董事长该回去了。”
“嗯。”沈从谦平淡地嗯了一声。
他提步往前走,醉酒后的人不太清醒,但从他面上看却看不出一点破绽。
沈从谦不是天生就会应酬的,时至今日他仍然不习惯。他天生酒量就浅,两三杯就醉。平日里他最多也就抿一两口敷衍一下,但今日场上有重要的人,这个面子他不能不给,只能硬喝。
回到家后,他脖颈上的牙印还在隐隐作痛。对着镜子,沈从谦伸手抚摸着这个鲜红的牙印。
这是宿泱给他的标记……
他心里涌起一阵又一阵的热流,冰冷的水从淋浴头一落千丈,但他的身躯却越来越热。
仅仅只是想起宿泱两个字,他就招架不住了。欲望因她而起,却无人能解。
从前他寡欲,对于男女之事没有太多的兴致,偶尔的疏解也是出于生理的需求。从未有过一次来的如此猛烈,他仿佛身处地狱,一生不得解脱。
风雨琳琅,人无处可躲,从里到外都被浸透,心也潮腻。游荡在人世间的圣佛也有片刻的失神,他扪心自问,生命还会如何存在?
如今他终于明白,爱是最伟大的法术。
为宿泱,他甘愿自囚。
宿泱回宿舍后,室友都已经在寝室了,见她回来都热情地打着招呼。
她们是四人寝,上床下桌。宿泱对床的姑娘一头棕色长发走路带风,她自我介绍说:“我叫陈印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