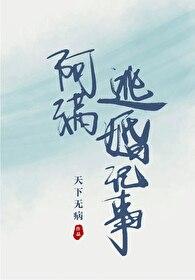02小说网>替身悔婚之后 > 第241章(第1页)
第241章(第1页)
久而久之,愿意提及阮州牧和阮家的人便越来越少,像是刻意地被遗忘。
但这两年,柳州牧却莫名收敛许多。
即便还是有所针对,可毕竟不会太过明目张胆。
阮瑟不禁有些许诧异。
个中种种如何,她原是再清楚不过。
一手摩挲着垂坠在腰间的玉佩,她旁敲侧击地问道:“柳州牧行事这么蹊跷,其中是发生过什么事吗?”
这厢反倒是换作秦夫人震惊难掩。
她低声惊呼道:“瑟瑟,你竟然不知道吗?”
“三年前,王爷曾在阮府小住几日,阮吴氏以为是你被赶回息州,带了不少仆从前去闹事。”
许是当时阮吴氏想要彻底败坏阮瑟名声,带人重回阮府时,亦着人在城中散了消息。
哪知最后这笑话落到她自己身上。
同天身败名裂的,还有柳州牧的嫡子。
嬴黎城中甚至传出阮吴氏与柳公子有染的荒唐流言。
尽管柳州牧及时差人去处理这些琐事、粉饰太平,可真相既定,做再多的辩驳都是欲盖弥彰。
“那阮吴氏而今身在何处?”阮瑟掩住所有心绪,“柳州牧对她……”
“不管不顾。”
秦夫人托住她的话,“我已经有好些时日没听到过阮吴氏的音讯了。”
早年还能偶闻两句,自今岁年节过后,她再没听到过阮吴氏母子三人的消息。
吴家更是当做不曾有过她这个女儿,险些将绝情二字都写在门匾上。
“你还想着见她?”
“虽然那算得上你的弟弟妹妹,可他们……”
“不见。”
未等她说完,阮瑟兀自截断她的话,美眸中笑意依旧,偏又裹挟着丝丝缕缕的凉薄,“父亲早年的遗书中,已将不少田产地契分给阮吴氏,足够她们一生衣食无忧。”
她自认不是什么以德报怨的好人。
阮吴氏训教她三年,从未待她有过好颜色,她又何必怀着那副好人心肠,再去嘘寒问暖。
只是……
阮瑟甫一想起赵修衍对阮吴氏的惩戒,仍有些置身云中雾里的错觉。
若仅是以下犯上,阮吴氏不会被毒哑音声,柳州牧的嫡子亦不会落到这般田地。
赵修衍既会如此,缘由再是明朗不过。
她临回西陈的那三年,他究竟背着她做了多少事?
谢家为其之一,息州诸事亦在其列。
偏生赵修衍从未宣之于口,任其掩埋于岁月荒风之中,或是久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