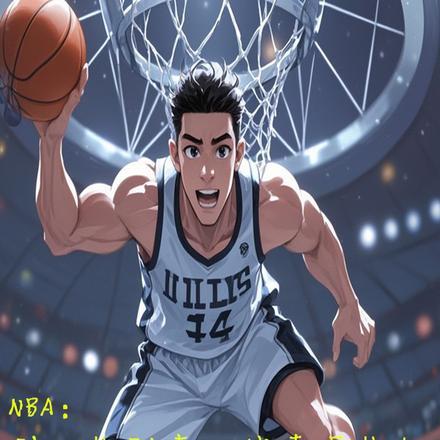02小说网>替身悔婚之后 > 第258章(第1页)
第258章(第1页)
琉月见自家公主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以为她还是在担心阮瑟,不由提议道。
崔婉颐怔神许久,回神后才反应过来琉月说了什么。
她迟疑地摆手,心下仿佛天人交战一般难以平息,却又半掺着很是奇诡的心绪,“不用。瑟瑟她会逢凶化吉的。”
毕竟有权势滔天的赵修衍护着她,阮瑟无论如何也不会陷入到这等求路无门的境地。
当务之急,是她要如何保全楚景瑞。
甚是苦痛地阖眸,崔婉颐挥手屏退琉月,只独身一人坐在榻上,单手支颐,清丽眉目间凝着无法消散的哀愁。
金銮殿中的所有音讯都事关重大,因而那场对峙也被埋没入枫红秋日中,零散在愈渐浓沉的桂花清香之中,只待尘埃落定之时。
宴觞居五楼。
雅间门前有暗卫看守,外间窗棂紧阖,遮盖轻纱。
明是天光大好的秋日艳阳,却硬生生笼罩出一种大厦将倾的威迫与沉闷。
南秦三皇子摇晃着酒盏,暗红酒液随之摇曳不息,勾抹出他眼底得意的笑容,“弃车保帅还是功亏一篑,殿下确实给雍王抛掷了一个上好的抉择。”
不论是那条分岔路,于赵修衍而言都是荆棘丛生、淌血剔骨的坎坷路。
只要一想到不可一世的赵修衍也会遇到要功业还是要美人这等两难的困顿,他的心中就生出一种很是轻快的愉悦,霎时卷席他全身,心旷神怡。
对面人同是愉悦神情,称赞道:“若是没有三皇子的一臂之力,雍王怕是早已脱困。”
他一早就预料到楚家行事不利,即便有沈太后相助也难以成行;南秦使臣的信,可谓是锦上添花,裨益甚广。
皇帝与赵修衍本就手足情深,楚家又是戴罪之身,罪证若是不足,阮瑟极易脱困。
更无法撼动赵修衍分毫。
可一旦有南秦涉足其中,诸般确凿无疑,即便赵修衍想包庇阮瑟都无从谈起。
骑虎难下也不过如此。
往来无用的寒暄话不宜过多,三皇子只笑不语,兀自陡转话锋,“怀州一事,殿下可曾安置妥当了?”
“切莫教雍王殿下再追查到蛛丝马迹。”
“自然。”
男子把玩着酒盅,如同把玩着势在必得之物,“那些人都已安排妥当,不留后患。”
“那些东西,他们应当已经送到南秦边陲了。”
“本殿都已差人前去接应。”三皇子点头,目光晦暗几分,“只是那场冲突到底是无妄之灾,教殿下担心这许久。”
以他的身份,做出这种交易显然是有违律法礼制。
从前四五次都安然无恙。
偏就这次,那些世家子弟为了多争一点微薄军功,相互之间争执不下,这才惊动了怀州的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