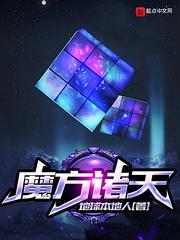02小说网>朕真不是中山靖王啊 > 第265章 刘胜 孤要亲亲相隐(第4页)
第265章 刘胜 孤要亲亲相隐(第4页)
“——非公室告,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
“但在老丞相的解释之后,儿臣才终于明白老丞相,究竟是想要说什么······”
对于天子启目光中的郑重、忧虑,刘胜自然是看在眼里。
至于天子启究竟在担忧些什么,刘胜心中,也是一片了然。
但对此,刘胜,却并没有丝毫担心。
“老丞相告诉儿臣:王子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罪,其实就是按照触犯法律者的身份,而给予相应的、不同的,且合乎身份的差别待遇。”
“——比如庶民杀人,当偿命;”
“官员杀人,当罢黜、罚金;”
“而权贵杀人,只需要给死者的家人做出赔偿,并取得其家人的原谅,就可以不被治罪。”
“在老丞相看来,这种现象和‘非公室告’,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根据犯法者的身份,以采取不同的处置、判决。”
面色澹然,而又自信的说着,刘胜不忘微微一笑,旋即稍侧过身;
对郅都浅笑盈盈的一拱手,便开口问道:“几年前,我的母亲和父皇游于上林,途中遇野彘一头;”
“当时,中尉还是中郎将,随行于父皇左右。”
“那一天,中尉并没有上前救我的母亲,而是因为担忧父皇的安危,便坚定地守护在了父皇身边。”
“——那件事发生时,我还年幼,并不懂得什么道理;”
“为了这件事,我和中尉之间,也曾闹出过些许不愉······”
“中尉,应该还记得吧?”
感受到刘胜语调中的随和,和隐隐表现出的善意,郅都纵是因为先前的事而感到不快,也只得僵着脸点下头。
便见刘胜又自顾自摇头一笑,继续道:“那件事后,我曾问过中尉:如果当时,父皇并不在场的话,中尉会不会上前救我的母亲?”
“我记得,中尉给我的回答是:会救。”
“但中尉救的,并非是我的母亲,而是父皇的姬妾······”
“我应该没记错吧?”
“这些话,是中尉曾对我说的吧?”
“既然如此,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我的母亲,和父皇之间并没有关系,那中尉,便绝不会上前相救?”
听闻刘胜此问,才刚勉强按捺住心中恼怒的郅都,却又陷入一阵纠结之中。
刘胜这一问,其实并不很复杂;
但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问,却将郅都推入了绝对的两难。
——当年,郅都并没有救当时的贾夫人,也就是如今的贾皇后。
对此,郅都给出的解释是:天下有无数个女人,也就可以有无数个贾夫人,但天子启只有一个。
换而言之,这对于郅都而言,是‘救天子启,还是救贾夫人’的选择题。
而此刻,当刘胜以此为依据,来提出‘中尉救人,也是看这个人值不值得救’的观点时,郅都即便是想反驳,也根本不知该从何说起。
因为无论话说的多么好听,郅都当年的行为,都正如刘胜方才所言:郅都,是根据被救者的价值,或者说身份,而做出了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