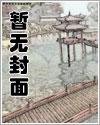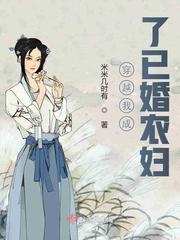02小说网>50个超真实罪案故事 > 第四章(第4页)
第四章(第4页)
“那他的杀人动机呢?”
“我在审问嫌犯时,曾经推断过一个合理杀人动机(小说前面刘嘉威和钱伟廉对话),在相关档案中有记载……相关推测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我咨询心理医师,再根据过往犯罪案例合理得出结论……简单说,凶徒具备这几个特征:
寻找目标是临时起意,犯案过程是多次模拟想象,为满足性心理,实际折磨虐待效果与嫌犯预期有落差,这是嫌犯最后没有进行**破坏处女膜,但却有割掉**原因,也可能通过**等方式满足,或者嫌犯无性能力。
致死受害者因为重手意外,最后大胆抛尸为失控的寻求刺激挑衅行为。
所有心理动机推测都有案例可循,这比你单纯说一句什么因为外部干扰所以最后没有强**体合理有说服力的多,既然外部干扰能停止**行为,为什么不能阻止嫌犯将尸体公然抛在街上?”
“你们是否调查过死者其他社会关系,以及与她有接触的强壮男性,比如死者男友,或者亲属?”
“当然……(犹豫)……没有可疑。”
“你们调查记录显示,陈怡丽所在夜校当夜值班记录及上课登记记录均消失不见,你们是否跟进调查?”
“是……当时曾经引起我们怀疑,那两份记录实际上并不正规,只是两张签到纸……可能只是被人随手当无用纸张丢掉……而且死者并无在夜校出现,因此我们觉得登记纸意义不大。”
“陈怡丽没有出现,但凶手却可能在登记名单上!”
“这只是你猜测……就算名单丢失,当日学生出席缺席情况我们仍然作了调查,而任课老师也都出现,正好可以做他们的不在场证明。”
“陈怡丽离家时说自己要替哥哥登载广告,报社你们去询问了么?”
“作了询问,可惜没有人承认当天见过死者。而时间上死者很有可能根本没有到报社去……因为死者最后约定和朋友见面的地点是六点半在跑马地车站,因此我们相信死者最后失踪地点就是在抛尸地附近,报社当日是否真去对案情均无影响。”
“纸盒上留下两个手印的人也没有找到了?”
“没有。”
“纸盒上没有我当事人指印,现场也找不到陈怡丽指印,而出现的指印你们却又找不到原主……这样办案态度是否太过儿戏?对我当事人是否公平?”
“我觉得没有问题……(下面一片哗然)……找不到被告和死者指印,正说明凶手犯案后认真清理过相关痕迹,一般来说凶犯在清理指纹时,会倾向把所有地方都仔细擦拭一遍,而不会按照自己记忆触碰过哪些地方去清理现场,因为自己可能遗漏场所,风险实在太大,不过有一种情况,他们会故意遗漏一些痕迹……
就是这些痕迹被发现,反倒对他有利!
我觉得被告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纸盒上有他本人的指印,我反倒可能怀疑我们抓错了人(突然感到说话困难,好像有痰卡住,刘嘉威吃惊,连忙咳嗽几下,才又能说话)……
还有你提到的西服为什么留下没被销毁,原因有两个:
一是凶犯并不知道我们现在侦破科技进步,已经可以查到如此细微证物!这些东西仅凭肉眼很难看到,要我们使用吸尘器和放大镜仔细观察才可……不夸张说,现场最后一排有人打个喷嚏,可能我们证物就再也消失不见了!(现场哄堂大笑,刘嘉威没有笑容)……
二是凶犯心思细腻,他一定想到我们如果怀疑他,必然要调查他当日活动,那么就会照例询问他参加同事聚会情况,会知道他曾经穿过一套正式西服。被告妻子没有工作,自己收入也很微薄,这样一套衣服可能是最昂贵,不可能轻易丢掉,我们如果找不到,反倒说明他有问题,所以他才把这么危险证物留下,被我们警察搜查拿走取证时,他可能反倒并不担心,只是棋差一着。”
“简直荒谬!试问哪个凶徒会这么冒险?”
“智商平庸的人自然不会……但是被告,聪明细腻极为注意细节,电器铺后面每一样东西摆放都极有秩序,家里录像带,衣物,鞋子用品都按照一定逻辑顺序,这样的人我和心理医师沟通过,其秩序性是来自于对细微事物超常观察的能力,是强迫症一种,他遇到是否丢弃西服这类两难问题时,会比常人想到更深一层,这样行为十分合理。”
第五日休庭:
舆论对现在案情走向看法分歧很大,有人就案件的疑点用阴谋论解读,认为凶手是被冤枉,大部分则认为虽然有疑点,但警方都给出合理解释,钱伟廉死罪难逃。
刘嘉威心情,并不好。
下午时,有两个女生突然来报案,被转到刘嘉威这里。
转过来的原因,“我们每日都要乘坐小轮由簸箕湾到观塘上学。曾经在船上出过事情。”
两个女生普通在校生打扮,白色裙子,齐肩短发,很普通,“什么事情?”
“我们被……”
“骚扰。”
“具体过程?”
两个女生互相对望,似乎都希望对方说出来。
“我们是看了这几天报道才鼓起勇气报警。”
“我们和死者陈怡丽是同一所学校,所以不希望那个被告逍遥法外。”
录完口供,刘嘉威看她们俩:“在这上面按一个手印。”
“你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