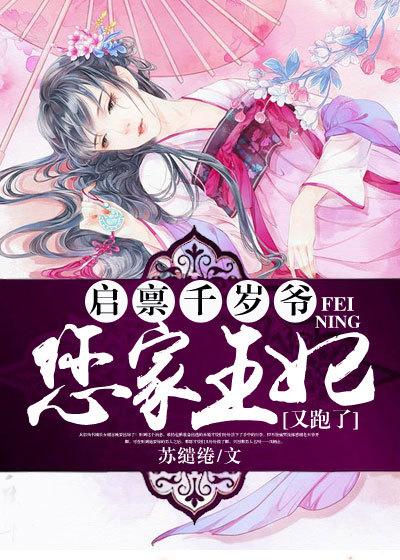02小说网>刺杀前夫失败后又重逢了 > 150160(第22页)
150160(第22页)
一想起昨日的事,她便气,低头一看,她的发丝在殿内的过堂风中轻轻摇着,并且似乎——是往他的方向招摇的。
她心里一惊,啪一声把那白子丢入棋盒。
嘉庆帝看了她一眼,抬手叫顾怀瑾起身,对她道:“珍妃,见了顾先生,连句话也没有?先生是朕敬仰依赖之人,连朕都不敢失礼,你怎么这样没规矩。”
南琼霜一凛,心知是昨日得罪了顾怀瑾,嘉庆帝怕他撂下挑子不干,上赶着笼络他,遂缓缓起身,转过来微微一拜:
“顾先生。”
虽则是彼此相对,可是不情也不愿,头也不抬眼也不睁,仿佛连瞧他一眼都懒得瞧。
他隔着绸带,静静望着她。
她固执地不肯抬眼对视。
顾怀瑾忽而觉得这一切很荒唐。
嘉庆帝为她不肯问安而斥她,他哪里知道,他们两个人,是谁巴巴地来求。
他来求了,她肯赦吗?
声名煊赫的人低三下四,福身行礼的人高高在上。
没人知道他在她面前穷途末路。
他喉结滚动:“娘娘不必多礼。顾某一介微身,娘娘乃一宫之主,顾某怎么好受娘娘的礼,皇上言重了。”
“是臣妾的不是。”她终于还是没看他一眼便转回身去,朝着嘉庆帝行了个规整的全礼,话说得利索:
“昨日同先生起争执,是臣妾一过;负气离去,是为二过;打了把名贵琵琶又弃之不用,奢靡无度,是为三过。臣妾知错。方才求皇上引戏班入京一事,请皇上万勿入耳。臣妾自知有愧,不敢奢求。”
说完,含着眼泪又行了一回礼,捻着帕子拭泪:“臣妾回菡萏宫思过去,请容臣妾告退。”
嘉庆帝听她低声下气一番话,心内欣慰,挥手将她斥下。
他期待又满意地望向顾怀瑾。
顾怀瑾面色更加苍白几分。
他不明就里,心中惶恐:“先生……”
顾怀瑾背对着她。即便他背着身,蒙着绸带,他仍是知道,她视他不见,擦肩而过,一路往殿门口缓行。两人越来越远,她的香气越来越飘渺,她出去了,云淡风轻。
顾怀瑾强撑着身形,只庆幸今日入宫缚了绸带,泪全兜在绸子里。
无情无义的狠心的人。
*
南琼霜今日到紫宸殿来,原是为了央嘉庆帝请彩庆班进宫唱戏。
没想到,才说了两句,就碰见了那人。
昨日他才给她扣了浪费无度的高帽,她不必提,也知道当着他的面,彩庆班是定然进不了宫,于是干脆不提了,脱身出来。
她径直去了大明宫。
李玄白刚刚下朝,朝服未更,坐在殿内忙里偷闲喝了盏茶,刚打开折子,便见吴顺引了她进殿。
见了她,他饶有兴致挑挑眉毛:“怎么,听说昨日你被那姓顾的气哭了?”
南琼霜懒懒朝吴顺瞄了一眼。李玄白当即会意,挥手叫他下去。
她没好气地落了座:“我也不知他什么毛病。”
“究竟是怎么了。”他笑着翻折子,“你并非眼皮子浅的人,他也并非牙尖嘴利之徒,怎么会为了把紫檀琵琶,当着皇上的面,一个怒斥,一个痛哭。”
她不说话,手里执一柄红鲤纨扇,心烦地扇着。
他意味深长地笑问:“当真交恶到了这地步,连在皇上面前,都忍不了?”
她登时知道他在试探什么,借坡下驴,将纨扇劈手砸在桌上:“你也不听听他昨日说的什么话!从无量山上下来,见我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下山愈久,看我就愈不顺眼,‘放过’二字,可是他亲口说的,如今又来找事!”
李玄白一阵笑。
她倾身过去:“你说他到底发的什么疯?我不过是玩了两日琵琶,没学成,放进了库房罢了——他这也要挑理!当着皇上的面,说要行节俭之风,一字一字跟我说要扣六宫的月银,人话?!”
李玄白端着茶盏啜了一口,被她逗得笑了,呛了两声,以拳头抵着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