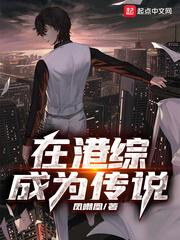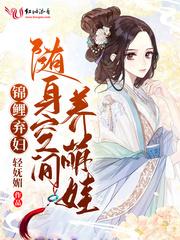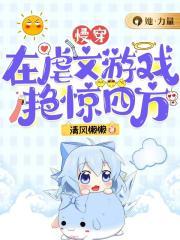02小说网>替嫁残将到底反不反 > 故人(第1页)
故人(第1页)
今日的安排被分开来,苏锦书和女眷们在兰亭苑一道,宁知远则和臣子皇亲去了曲水亭。
兰亭苑位于宫中东侧,离暖泉的尽头很近,当初杏林在此种植也有“日边红杏倚云栽”之意。
苏锦书来时尚早,便绕着去赏杏。兰亭苑晨雾未散,暖泉氤氲的水汽润得杏枝微垂,几星不合时宜的白蕊缀在青枝上。
苏锦书避了喧闹,沿泉徐行。绕过芍药丛,一片玲珑假山撞入眼帘。太湖石孔窍幽深,水光映照下,那嶙峋的轮廓陡然刺破尘封。
太熟悉了。
她脚步凝滞。
多少年前那个夜晚,也是这般迷阵似的假山。总角之年的她,宴中无人问津的影子,被反季杏花诱至泉边,最终迷失于此。
夜浓如墨,宫灯远如寒星,无人应她呼救,唯余放声恸哭……直至林氏牵起她冰凉的手。腰间玉佩虽不在,冰凉的触感仍旧贴着旧日惶恐。
仿佛一切都旧日重演一般,有一个脚步声极轻,自石隙传来。
她侧首回望。
一道身影自假山阴影徐步而出。晨光穿透石罅,为他周身镀上淡金。来人一身明黄常服,非是新制的辉煌,料子透着经年的柔软光泽,袖口衣襟处色泽略深,是半新不旧的温和质感。这颜色,这旧意……
苏锦书心口骤紧。
她难以置信地抬眸,正撞进一双含笑的眼。眼尾微挑,瞳仁清澈,映着泉光云影,带着浓密的睫毛和黑亮的瞳仁。
这张脸,俊秀昳丽,贵气天成,却又奇异地温煦可亲。
来的人正是李承泽。
明黄衣衫,半旧质感,明亮招人的眼……与记忆深处暖泉山石后探头探脑的小小身影,轰然重叠。
是他?那个寒夜里唯一与她说话、约定“明日见”的孩童?那个在她恸哭前匆匆离去的背影?
苏锦书喉间凝涩,怔然失语。所有猜忌、皇后的低语、缠枝莲纹的冰冷线索,皆被这穿越岁月的重逢撞得粉碎。她仿佛又成了那个假山前茫然无措的小女孩。
李承泽似未觉她心潮翻涌,唇畔笑意如晨风拂过杏蕊,温润亲和。
他迈步走近,声音清朗:“嫂子好雅兴,先一步来赏这盛夏奇景?”目光掠过泉边白杏,落回她面上。
是纯粹欣赏,抑或深宫锤炼出的滴水不漏?苏锦书难以分辨。腰间玉佩恍若突然又出现在她的身上,冰凉地硌着肋骨,无声叩问着那段尘封的无助。
“殿下。”苏锦书喉头微动,声音干涩得几乎不似自己。
万千疑问堵在胸口,化作一句恍惚的低喃,混着晨雾逸出唇畔,苏锦书忖度着说道,“这假山竟还是旧时模样。”
李承泽唇角的笑涡深了些,目光在她脸上逡巡,似在辨认旧痕。
“是啊,”他应得轻巧,指尖随意拂过身畔一块被水汽浸润得光滑的湖石,“宫苑深深,有些东西看着变了,骨子里却顽固得很。”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那嶙峋的石影,语气带着一丝难以捉摸的深意,“譬如这太湖石,看似孔窍通达,实则内里盘根错节,千百年风雨也难改其质。虽说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可是心头烙印,怕是比顽石要坚固几分。”
他的视线若有似无地扫过她下意识抚在腰间的手,那里曾经有玉佩温润的轮廓。
苏锦书指尖一颤。那目光温和依旧,却如细针,精准地刺破了她竭力维持的平静。
她猛地想起冬画的话:“承泽殿下身边的老嬷嬷,衣服上常带着缠枝纹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