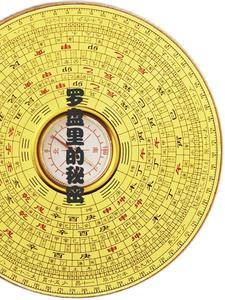02小说网>青梅竹马女友是公子哥的母狗 > 第21章(第13页)
第21章(第13页)
“以后每天洗澡都这样。”渤哥的声音像冰冷的刀锋,“互相洗,互相摸,摸到你们没有反应为止。”
“一个星期以后,谁要是还敢硬”
他眯起眼睛,目光像毒蛇一样缠上他们颤抖的身体。
这不是沐浴。
这是一场以“祛魅”为名的羞辱仪式。
而清儿,只是这场仪式里的工具。
我曾见过清儿眼里的光。
当她踮起脚尖在练功房旋转时,当她咬着牙压腿痛到流泪却不肯停下时,当她半夜偷偷对着视频矫正舞姿时舞蹈对她而言,曾是最接近信仰的东西。
就像她对我的依赖一样纯粹。
我曾经是她生命里的第一顺位。
舞蹈,则是第二。
可现在呢?
刘少的一条消息,一个随意的念头,甚至只是无聊时闪现的恶趣味都能让她毫不犹豫地践踏那份曾经的“神圣”。
他让她光着身子练舞,她就褪下所有衣物;
他让她在陌生人面前展示私处,她就叉开双腿;
他让她用最羞耻的姿态帮男生“祛魅”,她就颤抖着触碰别人的身体……
舞蹈不再神圣,而是成了羞辱她的工具。
而我,也不再是她生命里的“第一”,甚至连“必须遵守的底线”都不是。
现在的清儿,眼里只剩下一条准则:
“刘少的意愿,就是圣旨。”
哪怕那只是他随手打出的几个字;
哪怕那只是他突发奇想的恶作剧;
哪怕那只是为了满足他一瞬间的掌控欲……
她都会照做。
毫无犹豫,毫无底线,甚至……毫无挣扎。
曾经的清儿会因为练舞时的一个失误自责到失眠;
现在的清儿却能面不改色地在监控下分开双腿,只因为刘少说了句“想看她跳舞”。
多么讽刺。
最让我痛苦的,不是她变得淫荡……
而是她连曾经的“信仰”都能亲手打碎,只为了取悦那个把她当玩物的人。
而我?
我连“阻止”的立场都没有。
因为我早就不再是她生命里的“第一位”了……
下午4:30的夕阳斜斜地照进窗户,我在租住的小公寓里听到了钥匙转动的声音。
门开时,清儿拎着一只油纸包的烤鸭,脸颊被夏末的暑气蒸得泛红,发梢还带着舞蹈课后未干的湿气。
“宇哥!我买了刘记烤鸭!”她踮着脚尖在玄关换鞋,塑料袋哗啦啦响,“他们家的酱料可香了!”
我坐在餐桌前,看着她忙碌的背影。
她穿着普通的白T恤和牛仔短裤,脖子上我送的那条银色项链随着动作轻轻摇晃。
没有项圈,没有锁链,就像最普通的十八岁女孩。
这一刻的清儿,是只属于我的清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