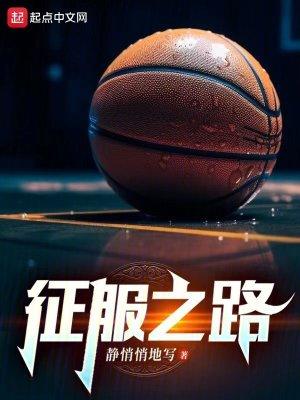02小说网>大宋文豪 > 第238章 成圣的途径(第1页)
第238章 成圣的途径(第1页)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继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
而相较于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是从四个方面对儒家义理精神进行了深化拓展。
分别是,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
陆北顾不久前所。。。
“学生陆北顾,拜见濂溪先生。”我再次躬身行礼,双手捧起早已备好的拜帖。那帖子用素白宣纸写就,字迹工整,上书“蜀中举子陆北顾,师承不详,学无专攻,唯知仰观俯察,格物致知。今岁入京备考,幸得程伯淳、程正叔引荐,得见先生,诚惶诚恐,伏惟垂察”。
周敦在旁轻咳一声,我便知机地将拜帖递上前去。濂溪先生接过拜帖,目光却并未停留其上,而是缓缓抬起,直视我面。那眼神清亮如秋水,却又似能洞穿人心,仿佛要将我二十年来所思所学,尽数映照出来。
“陆大友远道而来,想必对《太极图说》多有揣摩。不知对‘有极而太极’一语,可有心得?”
程颐在旁冷哼一声:“先生莫要被这等虚言所惑。蜀中僻处西南,士子多尚辞章,于义理一道,恐未深究。”
我心中一凛,知程颐素来严苛,今日特意考校,必不会轻易放过。当下不敢怠慢,正色道:“学生愚钝,然自幼好读《易》,尤喜《系辞》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之语。尝思太极为宇宙本体,动静相生,阴阳互根。然太极之前,果有‘有极’乎?抑或太极即是终极?”
濂溪先生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异色。程颐却冷笑道:“此等玄谈,有何实益?若不能贯通经义,终是虚妄。”
我正欲再言,忽听窗外传来一阵喧哗。只见几名监生模样的青年,醉醺醺地从廊下经过,口中还念着“金樽清酒斗十千”。其中一人脚步踉跄,险些撞到院墙边的竹丛。
“此等景象,便是国子监日常。”程颐摇头叹道,“昔日韩文公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之师者,多困于簿书,学子亦沉溺宴饮,何谈求道?”
濂溪先生却似未闻此言,只将目光投向那幅《太极图》,缓缓道:“陆大友既言‘太极即是终极’,可知太极之动静,实为天地运行之根本。然动静之间,又有几重境界?”
我沉吟片刻,答道:“学生以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此乃宇宙生成之序。然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动静相生,循环不息。若拘泥于动静之分,恐失其本意。”
程颐冷笑道:“此等泛泛之谈,便是蜀中所谓‘格物致知’么?若不能贯通《中庸》《大学》,终是隔靴搔痒。”
我知程颐素主“格物致知”,当下便道:“学生尝读《大学》‘致知在格物’,然何为‘格物’?朱子以为‘穷至事物之理’,王阳明却谓‘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学生愚钝,以为二者皆有可取,然皆未尽其妙。”
濂溪先生终于露出一丝笑意:“陆大友倒是敢言。然你可知,我作《太极图说》,实欲贯通天人,以明圣人之道?”
我正欲答话,忽见门外匆匆进来一人,正是国子监直讲张叔平。只见他神色慌张,低声道:“先生,宫中来人,说是要调阅《太极图说》原本。”
濂溪先生眉头微皱:“何人所遣?”
张叔平压低声音:“听说是枢密院张侍郎,说是奉了圣旨。”
此言一出,满室皆惊。程颐冷笑道:“枢密院插手国子监事务,倒是头一遭。”
濂溪先生却神色自若:“既是圣旨,便取去便是。然我这《太极图说》,不过粗疏之论,恐难当大任。”
张叔平犹疑道:“先生,那图中‘有极而太极’之语,若被误解,恐生争议。”
濂溪先生淡然一笑:“真理不辩不明,若有人能因此深思,亦是好事。”
正说话间,忽听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一名内侍打扮之人,带着两名小吏闯入院中。为首之人高声喝道:“圣上有旨,调阅濂溪先生《太极图说》原本,速速呈上!”
程颐勃然大怒:“此乃国子监重地,岂容尔等放肆!”
那内侍冷笑一声:“程侍讲莫非想抗旨不成?”
濂溪先生起身道:“无妨。”说罢,亲自取出《太极图说》原本,递与那内侍。
那内侍接过,随手翻了几页,忽然指着“有极而太极”一句,冷笑道:“此语颇有玄虚,恐非圣人本意。”
我见状忍不住道:“《易》云‘易有太极’,未言‘有极’,然‘太极’之前,若无‘有极’,则何以生两仪?此乃先贤深思之所得,非虚言也。”
那内侍上下打量我一眼:“你是何人,也敢在此妄言?”
我正欲答话,忽见院外又匆匆进来一人,正是欧阳修。只见他满面怒容,厉声道:“宫中之事,自有礼部尚书处置,何需尔等内侍插手!”
那内侍见是欧阳修,神色略显慌张:“欧阳大人,卑职只是奉命行事……”
欧阳修冷冷道:“既是奉命,便当知礼。此乃国子监重地,岂容尔等喧哗?”
那内侍只得收起《太极图说》,灰溜溜地离去。
待众人散去,濂溪先生叹道:“此图一出,恐又起纷争。”
程颐冷笑道:“朝中党争已久,先生之学,恐难独善其身。”
我见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辞。濂溪先生却道:“陆大友且留步。你方才所言‘太极即是终极’,颇有见地。然若欲深究,还需细读《易》《中庸》诸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