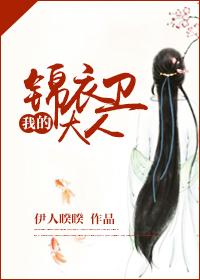02小说网>大宋文豪 > 第240章 紫袍大员(第2页)
第240章 紫袍大员(第2页)
陆北顾与植仪海并肩走出国子监,暮色沉沉,街市上人声渐起,灯火初上。然而,他的心却如古井无波,宁静而清明。两人沿着青石小路缓步而行,夜风微凉,吹动衣袂,带起几分秋意。
“陆兄今日所悟,可否言与我听?”植仪海忽然开口,语气平和,却带着几分探究。
陆北顾微微一笑,道:“今日听宋先生讲《为政》篇,又忆起先前在濂溪书斋所习‘主静立极’之功,方知修身、格物、致知,皆非孤立之事,而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若心不静,则志不坚;志不坚,则德不立;德不立,则政难行。故为政之道,实始于修身。”
植仪海点头,目光微动:“你果然有所悟。然你可知,宋先生为何要从《论语》开讲?”
陆北顾略一沉思,道:“或许,是要我们明白,为政之道,不在于策论之巧,而在于德行之正。若无德行之基,纵有良策,亦难施行。”
植仪海笑道:“正是如此。宋先生常说,理学之要,在于‘理一分殊’。天下之理,皆出于一,而分殊于万物。为政之理,亦是如此。若不知其本,纵知其末,亦难成事。”
陆北顾听得心中一震,道:“理一分殊……此言精妙。若能以此观天下,何愁不能明理?”
植仪海点头:“正是如此。你若能以此心观世,他日必成大器。”
两人一路谈笑,不觉已至城东一处茶肆。茶肆不大,却布置清雅,几张木桌散落其间,墙上挂了几幅字画,墨香犹存。陆北顾与植仪海择一临窗之桌坐下,小二端上两盏清茶,香气扑鼻。
“陆兄,你可知我为何要引你来听宋先生讲学?”植仪海忽然正色道。
陆北顾一怔,道:“莫非另有深意?”
植仪海轻轻点头,道:“不错。你自入国子监以来,虽勤学苦读,但心浮气躁,常为功名所困。我知你志向远大,欲成一代文豪,然若无静心之功,无修身之志,无格物之识,即便才华横溢,亦难成大器。”
陆北顾神色一凝,道:“兄所言极是。我此前确有急功近利之心,常因科举之压而焦虑不安。今日所悟,正是要以静心为基,修身立德,方能行稳致远。”
植仪海微微一笑,道:“你能有此悟,便是大幸。然悟而不修,亦无益。从今日起,你当每日静坐一刻,格物一理,修身一行,日积月累,方能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陆北顾郑重点头:“谨记兄言。”
两人又谈了些学问之事,直至夜深,方各自归去。
翌日清晨,陆北顾早早起身,沐浴更衣,焚香静坐。他闭目调息,依照濂溪先生所授之法,守定“无极之静默”与“太极之生机”,任思绪流转,不加抗拒,亦不强求澄澈。片刻后,心湖渐静,意念渐明,仿佛有一轮明月悄然升起,洒下清辉,照见心田。
他缓缓睁开眼,心中一片清明。起身洗漱,披上外袍,便前往国子监,准备听讲。
今日讲学,仍是明辨堂。陆北顾步入堂内,见堂中已有数人,皆是熟识的监生。他寻了个位置坐下,静待宋堂颐到来。
不多时,宋堂颐缓步而入,身着青衫,神情肃穆。他扫视众人一眼,缓缓开口:“今日所讲,乃《孟子?尽心》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诸君当细思。”
陆北顾心头一震。他知《孟子》乃儒家经典,讲“性善”之说,而“尽心”之道,正是理学修养之要。他屏息凝神,用心听讲。
宋堂颐继续道:“孟子言‘尽心’,即是要人尽其本心,知其本性,进而知天命。所谓‘天命’,非神鬼之命,而是理之命。理者,天地之常,万物之则。若能尽心知性,便可通达天理,顺应自然。”
陆北顾听得如痴如醉。他忽然明白,自己此前所求,不过是功名利禄,而今日所悟,才是真正的学问之道。学问,不仅是识字、作文、策论,更是修身、养性、明理。
“诸君,”宋堂颐目光如炬,“学问之道,贵在持敬存养,贵在日日用功,贵在不为外物所扰。若能如此,他日为政,必能以德服人,以理化世。”
话音落下,堂中众人皆肃然起敬,齐齐起身,向宋堂颐深深一揖。
陆北顾亦起身,心中一片澄明。他知道,自己已踏上真正的求学之路。
讲学结束后,陆北顾走出明辨堂,阳光洒落在院中那棵巨大的银杏树上,金黄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也在回应他心中的宁静。
他忽然想起昨夜与植仪海的对话,想起“理一分殊”四字,心中顿生明悟:天下之理,皆出于一,而分殊于万物。若能以理观世,以德修身,以心应物,便可真正明理、行道、成事。
他深吸一口气,目光坚定,心中默念:“心静,则理明;理明,则行正;行正,则德立;德立,则政行。愿以此心,行此道,不负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