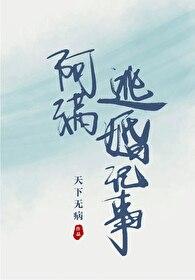02小说网>嫁给姐夫后 > 5060(第25页)
5060(第25页)
允乐端坐床沿,盖头未揭,身旁侍立着众多屏息的宫娥嬷嬷。
外间宴席的喧嚣渐渐散去,脚步声,人语声也归于沉寂,驸马该来了。
一位老成的嬷嬷走到门边,将窗推开一条缝隙探看,寒风裹挟着细雪倏地卷入,廊下灯笼被吹得摇晃不定。
不知何时,外面竟已飘起了鹅毛大雪。
除夕之夜,雪落无声,天地一片苍茫。
嬷嬷心中微有不悦:这些爷们儿,大喜日子也不知节制,被人起哄便一杯接一杯,醉醺醺的成何体统?难不成还要金枝玉叶的公主去伺候?
外头那些官员也该知些分寸才是。偏生那些攀附的官员,敬酒也不挑个时候,一杯接一杯,生怕驸马不喝他那杯酒。
风雪中,一道颀长身影由小厮搀扶着,踏着积雪踉跄而来,行至廊下灯笼光晕里。
嬷嬷眯眼细瞧,但见他唇角噙着一抹温润笑意,虽需人扶持,步履却无轻浮之态,更无寻常醉汉的丑态喧哗。
门扉轻启,带入一阵凛冽寒气。
夜深了,屋外的雪愈发大了。朔风裹挟着鹅毛般的雪片漫天乱舞,呼啸着拍打着门窗,发出沉闷的“咣当”声。
屋内却是一片暖融的静谧,
男人的声音带着酒后的微哑,低沉悦耳,带着歉意,“公主久候了,今日宾客盛情难却,多饮了几杯,实在失礼。”他面上因酒意染着薄红,举止间不见半分失仪。
允乐隔着盖头,颊边亦飞起红霞。
然而酒力终究汹涌,驸马刚与她温言数句,道了声“今夜实在失仪,有负良宵。”便支撑不住,和衣在床榻外侧沉沉睡去,他身量高大,躺下后竟占去了大半位置。允乐看着身侧呼吸均匀的男子,带着初为人妇的羞怯——
翌日清晨,
嬷嬷推门进来伺候时,只见允乐公主粉面含春,眼波流转,她身侧站着的章尧,经过一夜安眠,神清气爽,唇边噙着那抹惯常的温润笑意,愈发显得丰神俊朗。
更令嬷嬷暗暗点头的是,驸马爷竟亲自执了螺黛,正俯身为公主细细描画远山眉,动作轻柔专注,引得公主羞赧垂眸。
“公主请。”章尧立于马车旁,亲自为允乐撩起车帘,姿态体贴。
嬷嬷看在眼里,心中满意非常。
按礼,新婚后第一日,驸马公主需入宫觐见贵妃娘娘请安,允乐自幼养在贵妃膝下,与贵妃及二皇子情分匪浅——
大年初一的清晨。
秦国公一大早就出去锻炼身体,然后就把腰给扭了,下意识扭过头,避着点人的时候,被国公夫人看了个正着。
国公夫人劈头盖脸,把他一顿教训。
“还当自己是十七八的小伙子呢?”国公夫人看他那把老骨头已经脆的不行了。
秦国公要面子啊,被这么说了,自然是扭头就走,大儿子不会哄人,他掉头就往二儿子那里走,心里打好了一篇诉苦腹稿,谁知刚进门,话未出口,秦长坤只撑着下巴,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神色郁郁,连眼角余光都懒得扫他一下。
可把秦国公气坏了,这两个,没一个顶用的——
温棠抱着襁褓从国公夫人处回来,逗留了小半个时辰。幼子的名字已定下,唤作秦珩,端方雅正。
自然是秦恭取的。
温棠摸了摸衣袖那儿,然后把里面的玉佩取了出来。
昨夜辗转难眠,几番入梦。都怪睡前,她嫌秦恭一身酒气,便伸手捂了他的嘴,只让他露出一双眼睛。
秦恭的眼睛生得极好,深邃有神,目光锐利,不笑时威严肃杀,便是笑起来,眼底也淬着几分冷冽锋芒,
“凶神恶煞”四字,于他再贴切不过。
温棠摸了摸玉佩,心头涌上一股奇异的不真切感。
那时在山上,
温棠男人按住了不准走之后,先是把他打晕了,然后又小跑回来,丢了个馒头,正好砸中对方眉心那里,他晃晃悠悠地又倒了下去。
等他再睁开眼看她时,那目光,可真算不上友善。
出于良心的谴责,她才继续上山送饭。
他脸藏在阴影里,矜贵得很,进食时必背过身,慢条斯理。
起初温棠还道他教养好,细嚼慢咽。过了几日,那人才从大石后慢吞吞挤出两个字,“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