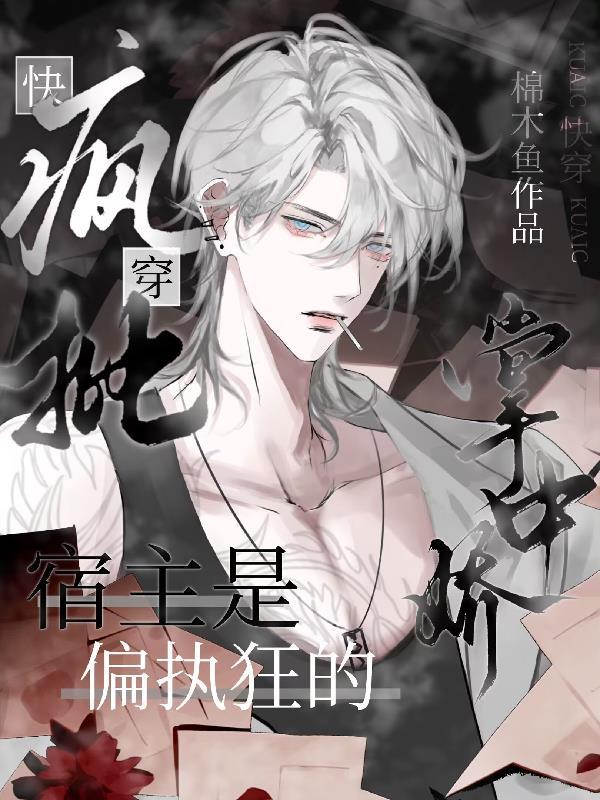02小说网>嫁给姐夫后 > 7075(第17页)
7075(第17页)
如今看着秦恭待温棠一片真心实意,她才算放下悬了多年的心,敢将当年压在心口的愧疚吐露出来,
那时她何尝不知女儿为何急嫁,只是自己既无康健的身体,又无玲珑心计,进了这京城高门,反倒成了女儿的负累。
温棠接过丫鬟捧着的药碗,小心地吹凉,一勺勺喂到母亲唇边,“娘,秦恭他只是性子闷,话少些,人却是极稳重的,您不必忧心。”
她没敢提秦恭如今私下里会闷着使坏了,在母亲眼中,姑爷还是那个威严端方,沉稳可靠的男人为好。
元氏自然知晓秦恭的好,只是为人母者,那颗心总免不了为儿女悬着,
她顺从地喝了几口药,抬眼看向女儿,嘴唇翕动了几下,眼中掠过复杂的情绪,似乎有话要说,最终却只是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咽了回去。
温棠垂着眼,专注地喂药,并未追问,母亲的心事,她约莫能猜到几分,
只是此刻,沉默或许是最好的回应。
直到暮色四合,冬日天短,再不回去,路上便要摸黑了,下人进来通传,
秦恭派来接人的马车已候在府外,他尚在宫中议事,未能亲至。
元氏忙让几个得力的丫鬟婆子,仔细护着温棠和周婆子回去。
人一走,屋内霎时冷清下来,只余炭火燃烧的微响和窗外呜咽的风声。
元氏半倚在枕上,望着帐顶,又是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叹。
清晨,她看见了阿福。
那时天刚蒙蒙亮,她辗转难眠,便让丫鬟服侍着穿戴厚实,裹了件披风,想去院中透透气,
推开门那一瞬,一个单薄的身影踉跄着从巷子尽头晃过,只匆匆瞥见一个憔悴的侧脸,但那身形轮廓,元氏几乎立刻便认出是阿福,
只那一眼,便消失在了风雪深处,再未出现。
方才,她几乎就要对女儿提起,可话到嘴边,终究还是被她用力咽下。
车轮碾过厚厚的积雪,缓慢前行,
车顶早已覆满厚厚的白雪,拉车的马匹口鼻喷着浓重的白气。
车厢内,周婆子听着窗外寒风呼啸,吹得帘子不时掀起一角,露出外面一片混沌的雪色,
她拢了拢衣襟,叹道,“这雪是越发大了,瞧着比往年都凶,天也冷得邪乎”
温棠点了点头,目光却越过周婆子的肩膀,望向车外,
周婆子先是一愣,心里顿时沉甸甸的,也跟着扭过头往窗外看,
阿福在茫茫风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头一直低着,
双手拢在袖中,露在外面的手指冻得通红。
周婆子当即转回头,嘱咐车夫把马车赶得更快些。
外面的阿福似乎有所察觉,猛地抬起头,目光正好对上前面的马车,
但他只看了一眼,便慌忙低下头,不敢再看,依旧默默地往前挪着步子。
雪片疯狂地砸落,很快便在他头上,肩上积了厚厚一层,
几乎要将他这具行尸走肉彻底掩埋。
雪势愈发暴烈,天色越发晦暗,
彻骨的寒冷让四肢百骸都失去了知觉,前方药铺门前悬着一盏昏黄的灯笼,在风雪中摇曳着一点微弱的光晕,透出些许暖意,
药铺的伙计瞥见这个雪人般摇晃走来的身影,“啪”地一声,关紧了店门。
阿福并未试图敲门,他只是默默地蜷缩在药铺门廊下那一点点可怜的,根本无法遮蔽风雪的角落里。
寒风裹挟着雪,打在他身上,
他拢紧的双手之间,紧紧攥着一张轻飘飘的,却又重逾千斤的纸,那是江夫人留下的遗书。
意识在极致的寒冷中开始模糊,飘散,阿福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一场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