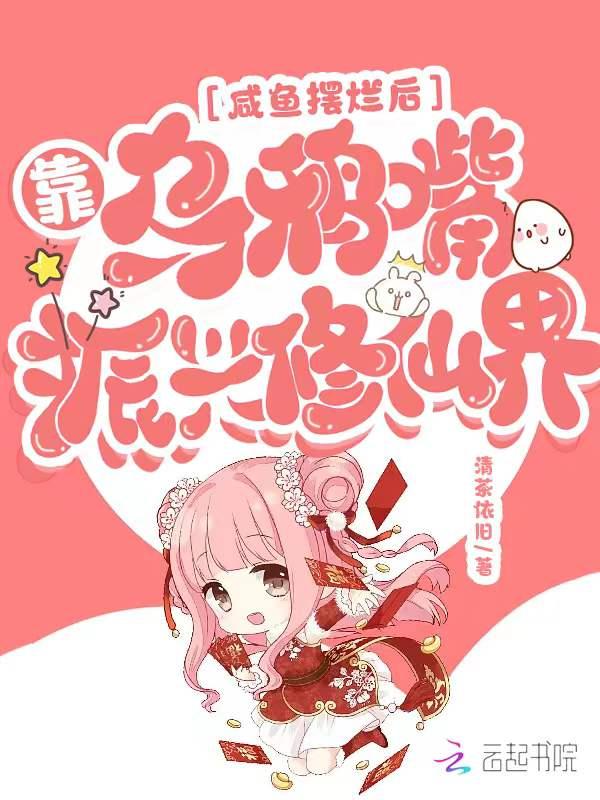02小说网>酿秋实 > 第二百一十四章 恨妒交缠(第3页)
第二百一十四章 恨妒交缠(第3页)
许是余幼嘉言语中的冷意太过明显。
那披肩散发的‘厉鬼’逐渐开始颤抖起来:
“不。”
“从一开始,就早早舍弃我了”
“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前朝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这是个官名。”
“若我这一生是话本,我被叫了半本书的周利贞,又被叫了半本书的‘谢上卿’”
,!
“所有人都从旁人口中听闻我的事,连你今日也是为那些事苛责我,可我问你,那个更像周利贞的人,告诉过你,我叫什么吗?”
余幼嘉蹙眉,下一瞬,却听他含泪开口道:
“寄奴。”
“我叫,寄奴。”
“我本是谢家用以待客的家妓之子,不知生父是谁,至十二岁也未有名讳,只被旁人称一句,寄奴。”
“谢家庭院深深,主君子嗣众多,我阿娘却偏偏以为只要我更像主君一些,让人觉得我是主君亲子,我们母子二人便能多得到一些,我装不像,她便会责罚我”
“世家大族的后院,磋磨人的法子,比刑书还要多。”
“比手指还要长的针,烧红后刺破皮肤,拔出后分明疼到骨髓,可皮肉上却只留一个有些像是黑痣的点,令人瞧不出更多”
早在那两个字吐出时,余幼嘉便已经僵化在了原地。
那些昔年的痛苦滚滚而来,终是如同他身上那些隐秘的黑痣一样,一一落到了实处。
他的不甘,愤恨,善妒
与那日城外他于破败马车中,抬头看向宛若天降的她时,那个莫名萌动的眼神,终究是有了缘由。
城外铃铎声仍然响彻余幼嘉的耳畔,但这回,她却终于能一窥他未被众人传颂的事迹。
他死死捂着脸,试图掩藏真容,又似乎,只是在掩藏过去狼狈不堪的自己:
“我是实在受不了打骂,才逃出谢家的”
“可自我十二岁得封上卿后,那些人又来找我,连阿娘都以投井威胁,几次三番让我想办法让她当主君正妻”
“每个人都看不到我,可我有用之时,他们又如蝗虫过境一样恨不得将我敲骨吸髓。”
“我恨‘谢’这个姓氏,我恨‘上卿’这个官名我,我还恨周利贞!”
“我恨他们,我恨那些自命清高的人,我恨为何没有人看到我,没有人愿意珍藏我,我恨四海之大,没有我的容身之所——
我就是恨这个天地!”
:()酿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