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子不类父?爱你老爹,玄武门见! > 第二百四十八章 传诛(第2页)
第二百四十八章 传诛(第2页)
而就在这一年冬至,龟兹方向再度传来消息:那位白发比丘尼圆寂前,留下遗言:“火不灭,矩不孤。持铃者虽去,然薪火已燃,遍布西域。”
与此同时,敦煌书院地下密室,最后一箱“崇文遗稿”完成誊抄。李昭亲自点燃蜡烛,照着墙上的目录逐一核对,忽然发现一处异常??在编号“丙七”的竹匣中,除了一卷《春秋左传补遗》外,竟多出一片极薄的丝绢,上面用针尖小楷写着一段从未见过的文字:
>“吾非阿罗檀亲传,乃其婢女之女。彼终生求‘矩火共生’,却不知真正平衡不在融合,而在分离??火属变革,矩主恒常。二者不可合一,亦不可互灭。故我另建一脉,不立庙,不传名,专司监察‘持矩者’是否已沦为新权柄之工具。今见子墨破镜自省,知时机已至,特献此言:
>**当‘守护真相’成为新的信仰,警惕它变成新的牢笼。**”
李昭浑身震颤,连夜唤醒子墨。
老人听完,久久不语。良久,才轻声道:“原来她一直在看着我们……不是考验我们能否守住‘矩’,而是看我们有没有勇气打破它。”
第二日清晨,子墨命人在书院后山立碑,无名,无字,唯刻一圈螺旋纹路,中心嵌一枚碎裂的铜镜残片。碑旁种下一株胡杨,据说是从焉耆古战场移来,曾见证三百守书人集体自焚的那一棵的后代。
春去秋来,朝廷对书院的围困逐渐松懈。或许是因民间风气已变,压制愈狠,反噬愈烈;又或许摄政王终于明白,有些东西,越是试图掩盖,就越会在人心深处生根发芽。
十年光阴流转。
子墨寿至八十,临终前三日,忽然睁开双眼??并非恢复视力,而是某种更深的觉醒。他对守在一旁的李昭说:“我听见了。”
“听见什么?”
“第九窟的钟声,第十窟的笔声,还有……未来的声音。”
他抬起枯瘦的手,指向东南方。“下一个他,已经在路上了。可能是个农夫,也可能是个宦官,甚至是个女子……只要她敢于在众人皆醉时写下第一个‘不’字,她就是持矩者。”
三日后,子墨安坐于石台,手握铜铃,溘然长逝。据目击者言,那一刻,整座书院的铜铃齐鸣,持续整整一刻钟,声震百里。飞鸟绕梁不去,风停树不动,唯铃音不绝。
葬礼简单至极,依其遗嘱,不用棺椁,不设牌位,骨灰撒入葱岭雪水,随流汇入敦煌河。唯有那支笔,被供于新建的“无名堂”中央,每日由一名年轻学子点燃一炷香,默念一句《寻矩律》。
李昭活到了九十二岁。晚年双耳失聪,却坚持每日到书院走一圈,用手触摸每一块石碑、每一本书架。有人问他是否还记得子墨最后的话,他笑着摇头,提笔写下四字:
**薪火不语。**
又三十年。
中原大乱,军阀割据,皇帝八易其主,史官尽数被屠,官方修史断绝。然而就在这个“无史之世”,各地突然涌现出大量手抄文献:有记录某城陷落时百姓互食的日记;有揭露某将军冒领军功的账本;甚至还有一份由宫女接力传写的《后宫实录》,详述三代嫔妃如何被药物控制、生育manipulated……
人们发现,这些文本格式惊人一致??开头总有一行小字:
>“谨遵《寻矩律》,年度自省录之一。”
而它们的传播路径,隐约连成一张网,源头指向西北一隅:敦煌。
某夜,一名流浪学者在荒庙避雨,点燃篝火取暖。他从包袱中取出半卷残书,正欲阅读,忽觉背后寒意袭来。转身一看,墙上影子竟不是一人,而是重重叠叠,似有无数身影伫立身后。
他颤抖着举起火把,照向墙壁。
赫然一幅新绘壁画:盲眼老者盘坐中央,膝上铜铃发光,周围九道光影环绕,第十道光则指向画外??正对着观画之人。
角落小字依旧清晰:
>“心矩所向,即是光明。
>光之所至,火亦为薪。
>薪尽火传,代代不绝。”
学者泪流满面,伏地叩首。起身时,他在庙门口发现一枚小小石片,上面刻着一个“矩”字,边缘磨损严重,显然已被传递过无数次。
他小心收起,继续踏上东行之路。
数月后,在江东一座书院中,一位少女接过这块石片,凝视良久。她出身寒门,因揭发乡绅伪造赈灾名册而遭驱逐,此刻正准备编写第一部《民间苦难志》。
她在灯下铺开竹纸,提起笔,蘸墨,写下第一行字:
>“余虽女子,亦知矩不可废。今录此事,非为复仇,但求一问:若天下皆伪,敢言真者,可是罪人?”
窗外,风起。
檐角铜铃轻响。
一如当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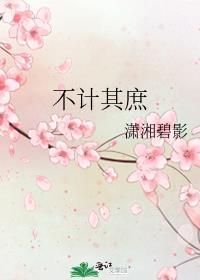
![女配她一心向道[快穿]](/img/5052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