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子不类父?爱你老爹,玄武门见! > 第二百四十八章 传诛(第1页)
第二百四十八章 传诛(第1页)
一池三山,千门万户。
在建章宫旧址上,人工挖掘的太液池,上筑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风水宝地,便是绣衣直指御史所在。
人称绣衣使,或者,诏狱。
来自大汉九州一百三十四郡的密报,源。。。
风自葱岭来,掠过敦煌城垣,卷起黄沙如烟。书院檐角铜铃轻响,一声接一声,不急不缓,仿佛与天地呼吸同频。子墨坐在院中石台之上,膝上铜铃静卧,指尖轻轻抚过铃身刻痕??那是第九窟崩塌那夜,他亲手以刀尖划下的“矩”字。如今它已微微发亮,像是被岁月磨出了魂魄。
李昭站在廊下,手中捧着一卷新抄的《寻矩律》副本,目光落在子墨背影上。多年过去,那人依旧瘦削如竹,脊梁却比当年更直。他的双眼早已看不见日月星辰,可每当风起时,他总能准确地转向声音来处,仿佛世间万物皆在他心中留有回响。
“昨夜又有三人自省书成。”李昭走近,将竹简放在石台上,“南疆来的那位,说他在查税吏贪腐案时,曾动念伪造证据,只因嫌正途太慢;河西守令坦承,为保一方安定,他曾压下一场民变实情,未报朝廷;最令人惊的是崇文馆老学士,竟承认自己删改过先帝遗诏注解,只为‘维系正统’。”
子墨点头,手指轻敲铜铃边缘,发出清越一音。“他们都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那便没死。”
两人默然片刻。远处传来孩童诵书声,朗朗如泉涌石隙。这是新一代寻矩使在晨课,所读并非经义章句,而是历代堕落者的自白录??那些曾几乎背叛“矩”的人,如何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
“你不怕吗?”李昭忽然问,“把这些污点公之于众?后人若见前辈亦曾动摇,会不会觉得‘矩’不过是个幌子?”
子墨笑了,笑容清淡如雪融于水。“正因为怕,才更要写下来。若只传光辉,不载阴影,那才是真正的伪。**真理不在完美无瑕,而在千疮百孔之后仍不肯熄灭。**”
话音未落,小童匆匆跑来??已是第三代“送汤人”,脸上还带着稚气,眼神却沉稳得不像孩子。“先生,西南急报!蛮部首领暴毙,其子夺权,宣称天降神谕,要焚毁所有汉文典籍,立‘赤火为尊’。已有三座藏书阁被烧,两名寻矩使失踪。”
李昭脸色骤变:“又是火教余孽?他们不是早在阿罗檀死后就散了吗?”
“未必是旧脉。”子墨缓缓起身,手扶杖端,面向南方,“但火种从未真正熄灭。只要人心尚存恐惧与谎言,它就会借尸还魂。这一回……恐怕不只是蛮地的事。”
果然,第三日,长安使者抵达,带来一封密诏。新帝年幼,摄政王代笔,言辞恭敬却暗藏锋芒:“闻子墨先生得窥第十窟真义,朕心甚慰。然近来民间妄议纷起,多引‘重写真相’之说,质疑祖制、诽谤宗庙,恐乱纲常。望先生能出山主持‘正史修纂’,厘清是非,以安天下。”
李昭冷笑:“这是要你去当刀,斩尽一切‘不合时宜’的真话!”
子墨却不怒,只将诏书置于铜铃之下,任风吹开。他虽不能视,却似能感知纸页翻动的节奏。“他们怕了。”他说,“怕的不是谎言,而是人们开始学会怀疑。从前只需一句‘奉天承运’便可镇住万口,如今百姓会问:谁写的天命?为何偏偏是你看见?”
“你要怎么回?”
“我写。”
当夜,子墨口述,由小童执笔,写下复奏:
>“臣盲且老,不堪重任。然有一言,愿以血荐轩辕:
>史非帝王之饰,乃万民之镜。
>若修史只为粉饰太平,则不如无史;
>若文字只能歌功颂德,则不如焚书。
>臣不敢奉诏,唯愿陛下思之:
>真相若需遮掩,那所谓‘安定’,究竟是护国,还是囚民?”
信使次日启程。李昭送至城外,望着驼队消失在黄沙尽头,回头叹道:“这封信一到长安,必遭清算。你可知接下来会是什么?”
“我知道。”子墨立于风中,衣袍猎猎,“先是贬斥,再是禁足,然后会有‘意外’。也许某夜书院失火,也许饮水有毒,也许路上突现刺客……但他们忘了,第十窟教会我的,不是如何活着,而是如何让‘矩’活得比我还久。”
果然不出十日,朝廷下旨,革除子墨“崇文馆顾问”之衔,禁止其门人入仕,并派兵封锁书院外围,名为“保护”,实为监视。更有御史弹劾李昭“结党营私,蛊惑士林”,责令交还勘误令。
那一夜,子墨召集所有尚在敦煌的寻矩使,共三十六人,齐聚第十窟投影之地??那片虚空中星辰坠落而成的书简平原。
“他们想让我们沉默。”子墨坐在石桌前,手中握着那支从第十窟带出的笔,“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无声胜有声’。”
他下令:即日起,《寻矩律》不再仅限内部传习,而是拆分为九篇短章,混入市井话本、医书药方、商贾账册之中,悄然流传。一篇讲“如何识破官府文书造假”,夹在《算经》附录里;一篇论“灾情上报中的隐匿之道”,藏于《疫病防治手册》末页;甚至还有以爱情传奇为皮囊,实则讲述“记忆如何被权力篡改”的小说,题曰《玉簪记》,已在酒肆茶楼广为传唱。
“我们要做的,不是对抗审查,而是让真实变得无法被彻底清除。”子墨说,“就像野草,哪怕火烧一遍,根还在土里。”
三个月后,奇事频发。陇西县令发现辖区内孩童竟能背诵《自省录》片段;洛阳书肆老板因售卖一本看似普通的《养蚕法》,被查出夹带《寻矩问答》而入狱,却在狱中组织囚徒共读;更有一名宫女,在为贵妃梳头时低声吟诵“心矩所向,即是光明”,当场被捕,审讯中坚称:“奴婢只是听街头说书人唱的。”
风波愈演愈烈。朝中开始有人悄悄议论:莫非这天下,真的不能再靠瞒与骗维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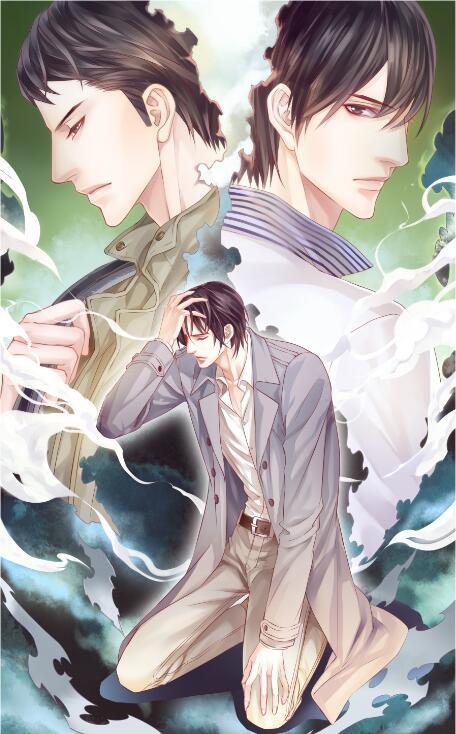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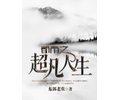
![[红楼]我成了宝玉的哥哥](/img/19965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