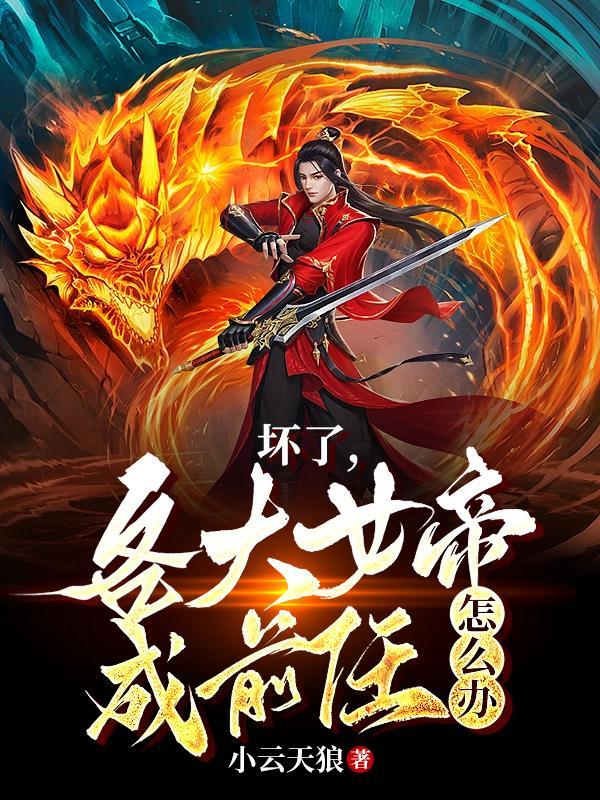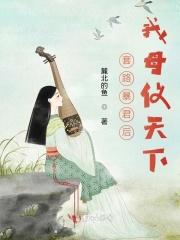02小说网>明末封疆 > 第602章 稳住时局(第1页)
第602章 稳住时局(第1页)
凛冽的北风依旧在燕山群峰间尖啸,卷起枯枝败叶,却再也吹不进紫禁城那高耸的红墙。墙内,一种截然不同的暖意正在凝聚、升腾,驱散了数月前国破家亡的阴霾。这暖意,是劫后余生的喘息,是力挽狂澜的决心,更是大明虎贲枕戈待旦带来的、沉甸甸的希望。新入宫不久的小宫女福香,正屏息凝神地用拂尘掸拭着御座上的微尘。她记得刚来时,这里弥漫着散不去的血腥和绝望气息,宫人们走路都踮着脚,生怕惊醒了什么。如今不同了。虽然陛下依旧面容清癯,但眉宇间的郁结已化开不少。透过半开的殿门,他能听到几位重臣沉稳有力的奏对声,其中那个被称作“魏柱国”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铁石落地,让整个大殿都安静下来。福香偷偷抬眼,瞥见阳光透过窗棂,斜斜地打在光洁的金砖地上,映出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报——不再是告急的文书,而是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四省源源不断传来的“安民复耕”、“厘清田亩”、“流民渐归”的消息。这四省,真如巨人复苏的四肢,将力量源源不断地输回京师这颗重新搏动的心脏。福香下意识挺直了腰板,连掸尘的动作都轻快了几分。千里之外的辽西走廊,寒风如刀。老卒王铁柱裹紧身上半旧的棉甲,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刚立起不久的哨堡间巡夜。脚下的土地,几个月前还是大清游骑耀武扬威的地方。他摸了摸脸上那道从通州血战留下的伤疤,又抬头望向更北方的黑暗。魏柱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名,王铁柱不懂那些文绉绉的话,但他亲眼见过:几队凶悍的蒙古骑兵押着几个满洲探子的尸体来到营前,用生硬的汉话喊着“归顺魏帅!”,然后放下人头和几匹好马就走了。营里懂蒙语的兄弟说,草原上都在传魏渊的名字,说他用兵如神,是“天狼星下凡”,专门克那些满洲鞑子。王铁柱咧嘴无声地笑了笑,粗糙的手指紧紧按在冰冷的刀柄上。这向前推进的几百里,每一寸都是用血和魏帅的威名换来的。他深吸一口凛冽的空气,觉得格外踏实。能活着,能守住,就是最大的福气。西北的寒风格外刺骨,卷着沙砾抽打在脸上。破旧的营帐里,火头军老张头正费力地搅动着大锅里稀得能照见人影的杂粮糊糊。柴火湿,烟大,呛得他直咳嗽。锅里翻腾的,与其说是粮食,不如说是信念。几个月前,他们几乎断了粮,连马皮都煮了吃,是孙传庭将军硬生生用军令和身先士卒稳住了快要溃散的军心。“老张头,省着点柴!这鬼天气,还不知道下一批粮秣啥时候能到!”一个冻得嘴唇发紫的年轻士兵抱着胳膊缩在角落嘟囔。“省?再省就喝西北风了!”老张头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但搅动的勺子还是下意识沉了沉锅底。就在这时,营帐门帘被猛地掀开,一个浑身裹满冰霜、几乎不成人形的身影踉跄着扑了进来,嘶哑地喊道:“信!北线信使!京师的粮……军械……到了!还有……蒙古人……归附……送来了马匹皮毛!”整个营帐瞬间死寂,随即爆发出压抑的欢呼!角落里那个年轻士兵猛地跳起来,冲到信使身边,眼睛死死盯着他怀里那个油布包裹。孙传庭闻讯大步走来,他身上的铁甲同样布满寒霜,但腰杆挺得笔直。他接过包裹,借着昏黄的篝火,迅速扫过那份由朝廷印信封缄的文书。火光映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那双因长期缺粮和操劳而深陷的眼睛,此刻亮得惊人。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将那封带着京师暖意的文书紧紧攥在手心,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京畿的支援虽少,却像投入死水的巨石,激起的不仅是涟漪,是活下去、打下去的希望!他转身,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老张头,今晚,锅里多放一把米!”京东卫所的校场上,杀声震天。莫笑尘,这位辽东基层提拔起来的年轻将领,鹰隼般的目光扫过操练的新兵方阵。他一身洗得发白的旧战袍,腰悬佩剑,背着手在队列中穿行。“腿!站稳!腰腹发力!想象你面前就是鞑子的咽喉!”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鞭子一样抽在每个新兵的心上。一个年轻士兵动作稍慢,莫笑尘的手闪电般探出,在他膝弯处不轻不重地一点,那士兵顿时一个趔趄,脸涨得通红,却咬着牙立刻站稳,动作更加用力。莫笑尘微微颔首,目光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这些新兵蛋子,底子差,但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他知道魏渊在后方殚精竭虑整顿工部、开埠通商,运来的崭新制式刀枪和棉甲正一批批送到营中。有了这些,再加上严苛到近乎残酷的训练,他们才能从农夫蜕变成战士。,!与此同时,在山东大营,秦牧阳则展现了另一种风格。他更像一个严厉的师傅,亲自示范着每一个格挡、刺击的动作,讲解着战场上的生存之道。他嗓门洪亮,骂起人来毫不留情,但新兵们私下却服他,因为他教的都是保命的真本事。他时常拍着新兵的肩膀,指着远处操练的、眼神锐利、沉默寡言的老兵队伍说:“看见没?那是从通州、京师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爷们!想活命,想和他们一样成为朝廷的倚仗?那就把吃奶的劲都给我使出来练!”10万大军!这个数字沉甸甸地压在永熙朝廷的基石上,也点燃了每一个知晓内情者的心火。这不再是溃散的流民,不再是绝望的孤军。6万百战老卒,他们是朝廷的脊梁。在辽东,他们曾用血肉之躯阻挡过建奴铁蹄;在通州,他们曾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他们的铠甲上布满刀痕箭孔,沉默寡言,眼神却像淬火的刀子。他们是魏渊整合各方力量的核心,是莫笑尘、秦牧阳训练新兵时最好的榜样。一个眼神,一个新兵就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战场。4万新锐之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在莫笑尘的冷酷鞭策和秦牧阳的严厉教导下,在崭新的刀枪铠甲武装下,他们褪去了青涩。虽然还未经历大战的洗礼,但严格的军纪已刻入骨髓,高昂的士气如同即将出鞘的利剑。他们看着身边那些伤痕累累却如山岳般沉稳的老兵,眼中充满了敬畏和向往。薪火,正在悄然传递。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京畿的薄雾,洒在巨大的校场上。数万将士披甲执锐,肃立如林。刀枪如麦穗,反射着冰冷的寒光;旌旗蔽日,在风中猎猎作响。那肃杀之气凝结成无形的屏障,比燕山更巍峨,比北风更凛冽。老兵的目光沉稳如古井,新兵的眼神炽热如火炭。他们共同构成的,是永熙朝廷在惊涛骇浪中稳住舵轮后,最坚实、最无畏、足以让整个北国为之侧目的底气!这艘巨舰,终于再次扬起了风帆,朝着未知却也充满希望的深蓝驶去。天津卫,这座曾因海禁而略显萧索的北方门户,此刻仿佛被魏渊的“开埠通商、兼收并蓄”八字符咒点醒了沉睡的魂魄。短短半年光景,它便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沸腾着五洲四海气息的奇幻熔炉。海风裹挟的不再仅仅是咸腥,而是金钱、梦想、新奇与碰撞的喧嚣热浪。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大沽口码头已如苏醒的巨兽般吞吐不息。粗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压过了海浪的拍岸。力巴老三,赤着古铜色的精壮上身,肌肉虬结如老树根,正扛着巨大的檀木箱,脚步沉稳地踏过颤巍巍的跳板。汗水在他脊背上汇成小溪,滴落在沾满鱼鳞和碎木屑的甲板上。箱子里散发的奇异香料味直冲鼻腔,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引来旁边一个正指挥水手卸货的红毛番商不满的嘟囔。老三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用浓重的天津腔吼回去:“嚷嚷嘛呀?爷们儿扛得动!加钱管够,千斤顶也给您扛家去!”那红毛商贾显然听懂了“加钱”二字,耸耸肩,摸出几枚亮闪闪的西班牙银币抛了过去。叮当脆响中,老三的笑容更灿烂了,脚下的步子也仿佛轻快了几分。桅杆如密林刺向灰蓝的天空,各色旗帜猎猎招展。梳着月代头、腰挎长短刀的日本浪人武藏,紧抿着嘴唇,鹰隼般的目光扫视着自家货船。他并非商人,而是受长崎豪商所托,护送这批珍贵的精铜和漆器。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刀柄,眼神深处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码头上随处可见张贴的告示,上面是大明律令的条款和魏渊的画像。每当看到那张年轻却威严的面孔,宫本便会微微低头,心中默念着故土流传的神话:“魏柱国……平定东瀛、扶立女皇的‘神君’……”他身旁一个年轻武士正生涩地用刚学的汉语与税吏交涉:“大、大人,倭国铜,上品!请、请关照!”税吏板着脸,却指着告示上清晰的税率条目,示意他看。年轻武士慌忙点头哈腰,不敢有丝毫造次。对“神君”治下的律法,他们奉若神明。离开喧嚣的码头,步入天津卫新拓的街衢,一股更复杂、更诱人的气息扑面而来。新建的货栈连绵不绝,高大气派。店铺门前幌子招摇,写着“苏杭绸缎”、“闽粤香料”、“泰西奇珍”、“东洋漆器”……琳琅满目,晃花人眼。“顶好的法兰西玻璃镜!照人毫发毕现,赛过龙宫水晶宫喽!”一个留着两撇鼠须的广东牙人,操着半生不熟的官话,唾沫横飞地向一位衣着光鲜的本地士绅推销。那士绅矜持地用扇子拨开几乎戳到脸上的镜子,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镜中清晰的自己吸引。:()明末封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