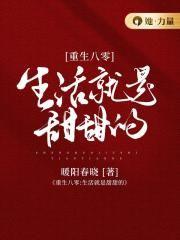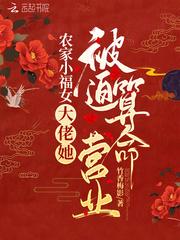02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60章(第1页)
第60章(第1页)
“当时我的观察是,民兵的逐渐消亡,其实是基层管理和组织逐渐减少的一部分。全国和全民转向经济发展,基层管理和组织这种太过革命化的安排,似乎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且成本太高,似乎有正常的各级政府机构存在,就足够了。实际上,这是去革命化的一部分。”
“当然,这种基层弱化的趋势,在后来遭到了不少反噬。例如新疆和西藏被煽动起来的恐怖活动;例如落后地区的乡村,重新落入贫穷而瘫痪的境地,东莞当时有的小姐,居然回乡过年,还要到村长家“值班”,村长完全变成了恶霸;例如某明珠大城市,在抗疫中表现出来的基层涣散和无能为力。”
“从2010左右开始,对于基层涣散,上层建筑有所重视,但说实话,除了新疆这样的重点反恐地区,改进幅度有限。”
毛泽东的神色非常严峻:“基层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一定有别有用心的人,会去占领。”他对于李思华前世这些“沉渣泛起”的丑恶现象,尤其是落后乡村的治理瘫痪,痛恨至极。
所以两人一致同意,必须长期加强,而不是逐渐降低对基层的管理和组织。
李思华说:“我们的民兵组织,真正在建国后,我想将之与教育和基层组织干部体系,结合起来。”
她解释说,如果保持10%的人口比例是民兵,那么这10%主要就是选拔次优的年轻人,最优秀的可能进入大学或者军队。这批次优的人,也可能在年轻人比例中要占到25%或以上,建国6亿人口的话,要超过6000万人。那么多的人组织起来干什么呢?就在本地作为当地的青年积极分子的先锋队吗?激情能够保持多久?尤其是农村,一帮乡村青年,能有多少见识,带动当地的发展和思想进步?
所以要让他们教育起来、流动起来。
“在教育方面,建议在城市和乡寨,都要设立民兵流动教育站。城市和乡寨中,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经济组织的管理人员,都要作为长期兼职的教师,还可以专设一些专业教师。他们对来到城市和乡村的民兵进行教育,或者是政治思想,或者是自然生态、动植物知识,或者是农业种植养殖科技,或者是加工业的经营和管理,或者是机械电气操作,或者是企业的组织和管理。”
“这样的流动教育,如果一个民兵在各地经历了三年或以上,尤其是乡村青年,几乎可以肯定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一个远比过去,呆在自家乡村要有能力、有思想的人。”
“在流动方面,建议每个民兵要打散,三三两两地分入其它地区的民兵组织,而不是在当地。每一年轮到一个地域,参与当地乡寨或者是城区的工作,担负最基层最繁琐的工作,担负劳动任务。白天工作,晚上夜校,全面占领他们的时间,让他们在劳动、学习、工作锻炼中,逐步成为我们理想的接班人。”
“如果建国初期,我们实行九年业务教育,从7岁开始上学,那么16岁是初中毕业,学习优秀的人上高中,部分上技校或中专,两部分的人员大约25%足够了;其余的75%青年中,25%就选拔进入民兵。”
“从16岁到21岁,总共是5年,每个民兵应该在各地轮流驻扎5个地域,每年1个。例如从四川到陕西,再从陕西到山西,从山西到内蒙,从内蒙到新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选择基层干部的过程,也是一个大移民的过程,在5年完成后,尽量劝说他们在外地,尤其是祖国需要的地方安家落户,还可以带动他们的家人,前来新的地方安家。”
“这样大规模地流动起来,大规模地教育起来,大规模地训练和组织起来,大规模地在异地参与劳动、生活和工作。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拓宽了眼界,学到了能够实践的知识和本领,思想得到极大的拓展,就能够告别愚昧、拥抱现代化。未来的村长村干部、乡长乡干部、区长区干部、街道干部,主要就来自这个民兵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半军事化的一面并没有弱化,但其它的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就是一个超级干部学校、超级教育学校、以及一只超级劳动力大军。”
毛泽东倒吸了一口冷气:“你这是要让全国都流动起来哈,六七千万人,成本能撑得住吗?”
他发现他和李思华谈话,总是很难坐得住。或许是因为她时有惊人之语,让人难以平静下来的缘故。
李思华认真地点了点头,解释说:
“我自己仔细想过,成本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这个大计划实施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粮食,这一点我们下次再讨论。”
“如果有足够的粮食,那么问题就不大,耗费主要是在交通上,在路途中除了消耗粮食,住宿是帐篷、行动要靠运输发生成本,但到了地头,他们其实是替换了本地的民兵,充当当地新的劳动力,并没有增加新的人员,当地的粮食消耗并没有增加。”
毛泽东兴奋了起来,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开始走步思考,一时仿佛忘了李思华还坐在那,让她感觉有点好笑。
毛泽东却顾不上,他想象着这样做的好处,每个乡寨和城区,每年不断有在各地获得各种本领和经验的民兵前来,替换成为当地的生产人员,他们为原来封闭的当地小圈子,带来了巨大冲击,不但他们自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从普通青年到革命战士的转变,而且用他们的见识、经验和热情和组织,可以带动本地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可以提供新的思想思路,可以打破原来千年不变的宗族、陋习,让当地的民情风尚,焕然一新。
李思华曾经和他说过,前世解决就业难题,是靠尽量推迟青年人的就业时间,尽量都上高中,到后面尽量都上大学,平均就业年龄因此推到了20岁之后,因为社会实在无法提供那么多的职业。这样的普及,实际上降低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结果是太多的青年,等到22岁大学毕业后,没学到什么本领,大量的人最后也只能家里蹲,或者从事一些最简单的工作,例如送快递,这样的浪费下,多数人的大学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李思华的这个计划,通过民兵组织这一形态,让大量青年,经过5年伴随高度实践的教育和工作,到这些青年21岁后,生存的本领、成熟的思想、实际工作的能力,恐怕反而会超过前世,甚至超过很多,实践出来的。
他停了下来,转向李思华:“所以问题就在于经济成本?这个计划非常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起来才能让革命深入,这也能打破地方主义和在地方上形成新的势力固化!”
李思华补充说,这也是教育过程,5年过后,我们也发文凭,相当于大专毕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准备,并没有弱化,这5年本身也包含了军事训练的内容,恐怕这样反而能够学得更多。
主席非常同意这点,比较关键的束缚,即经济成本,需要算细账,如果开始支撑不了,那么人数就减少一些,逐步再增加。
第99章抗日整军与公有制激励
李思华非常赞同主席所说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她说道: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一定不能让新中国的乡村和城区,再继续保持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很多的地方,不是没有好的资源和发展进步的机会,而是没有发展的热情、没有发展的思路、没有团结改变的决心和意志。愚昧和懒政,始终动摇不了,甚至沉积和发展。”
主席笑了笑:“所以民兵组织就是一条超大的鲶鱼,让整个中国活跃起来、行动起来、进步起来;民兵组织也是一股洪流,让它冲走整个中国旧社会上蓄积的沉渣烂滓,例如什么外地人歧视、乡土圈子之类的垃圾文化。我们就是要搞事,搞到整个中国的传统社会都流动起来,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