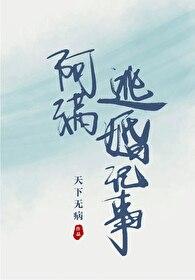02小说网>种田系统让我攻略病娇世子 > 王妃(第3页)
王妃(第3页)
正中的罗汉榻上,端坐着一位妇人。约莫四十许年纪,穿着深青色莲纹的锦缎袄裙,发髻梳得一丝不苟,簪着两支样式简洁的碧玉簪子。
她的容貌依稀能看出年轻时的秀美,但此刻脸色苍白,眼下有着浓重的青影,眉宇间凝结着化不开的疲惫和深深的忧虑,像被千斤重担压着。
这便是南阳郡王的王妃,赵世子的生母,柳氏县主。
柳氏县主目光沉郁,像两潭深不见底的寒水,落在林幺幺和李翠花身上的视线,带着一种无声的威压。
仅仅是被这目光扫过,李翠花就腿一软,“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带着哭腔:“民妇李翠花,叩见县主夫人!夫人开恩啊!”
林幺幺也跟着跪下,循着记忆中模糊的古礼,规规矩矩地磕了个头:“民女林幺幺,叩见县主夫人。”
“抬起头来。”柳氏县主的声音不高,却自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林幺幺依言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落在柳氏县主膝前的地面上,没有直视,姿态恭谨却不卑微。
柳氏县主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片刻,跪在眼前的小村姑,年纪不大,穿着粗布衣裳,却有一双异常清澈沉静的眼睛,在这样目光下,竟不见多少慌乱。
目光微移,落在了旁边抖如筛糠的李翠花身上。
如此鲜明对比。
嗤。。。倒是有趣。
“昨日,”柳氏县主缓缓开口,每一个字都带着冰碴子,“我儿在你们店里用了你做的吃食,回去半路便呕血不止。此事,你们该作何解释?”
她此刻转脸面向了李翠花,那压力让李翠花几乎瘫软在地。
“夫人!冤枉啊!”李翠花抖着身子哭嚎起来,“都是这丫头!是她做的那个什么火锅!民妇……民妇也是被她蒙蔽了!请夫人明鉴啊!”她毫不犹豫地将所有责任推给了林幺幺。
柳氏县主的目光又落回林幺幺身上,带着更深的冷意。
林幺幺心中哂笑,对李翠花的行径毫不意外。
她再次俯身叩首,声音清亮坚定:“回禀夫人,昨日世子在醉香楼所用汤食,食材皆为醉香楼厨房所出,民女仅负责烹制调味,所用菌菇、山药、干贝,皆性味平和清淡,同时油盐减半,绝无大补大燥之物。此其一。”
她微微直起身,继续道:“其二,若真是汤食中毒,小公子当有腹痛、腹泻、呕吐不止等急症,而非仅呕血。且民女后来所献姜蜜水,性温甘缓,若为中毒,断不会立时见效。”
“所以民女认为世子饮后呕血立止,面色转缓,正说明其症结在‘虚不受补’或‘气血冲逆’,而非外邪入体或中毒。”
她这番话说得条理清晰,虽用了些医学术语,但解释得浅显易懂。柳氏眼中闪过一丝惊异,旁边的孙嬷嬷也不由的皱起了眉头,仔细听着。
“其三,”林幺幺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谨慎的试探,“民女斗胆一问,昨日为小公子递汤时,曾闻到公子身上极淡的药味。后来公子呕血,民女……曾在旁留意,其呕吐之物中,除却汤水,似……似有一丝难以名状的辛涩之气,非汤底所有。
林幺幺停顿了片刻:”容民女大胆揣测,是否公子日常所服汤药之中……有药性过于峻烈,或与公子体质相冲之物?所以昨日汤水入腹,引动药性,才致急症?”
“放肆!”孙嬷嬷厉声喝道,“世子用药,皆由名医斟酌,岂容你一个乡野村姑妄加揣测!”
林幺幺立刻伏低身子:“民女惶恐!民女不敢妄议名医!只是心忧公子贵体,将所见所感据实禀告夫人!若有失言,甘受责罚!”她姿态放得极低,但话里的意思,却像一根刺,精准地扎进了柳氏县主心中那根最敏感的弦。
柳氏县主放在膝上的手,猛地攥紧了手中的锦帕。
她面色虽不见任何反应,但眼里神色剧烈地波动起来,里面翻涌着惊异、怀疑,还有一丝被压抑了许久的、不敢深想的恐惧。
儿子久病不愈,汤药从未间断,却日渐衰弱……难道…真如此。。。
屋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李翠花压抑的抽泣声和林幺幺沉稳的呼吸声。
阳光透过窗棂缝隙,投下一道细长的光柱,尘埃在光柱中无声飞舞。
良久,柳氏县主才缓缓松开紧握的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却努力维持着平静:“你……还懂药理?”
“回夫人,民女不敢妄言。”林幺幺依旧伏着身,“家中祖父曾是铃医(走方郎中),留下些粗浅的食疗方子和辨识药性的土法,民女自幼耳濡目染,略知皮毛。”
“所以民女今日前来,一是请罪,二是斗胆献上几份专为脾胃虚弱、厌食体虚之人拟的食疗方子,皆以常见食材为主,性味平和,或可辅助调理公子贵体。”她说着,从怀里取出那个小小的粗布包裹,双手捧过头顶。
孙嬷嬷上前接过,打开看了一眼,是几张写得工工整整的纸,上面列着几份食谱,用料果然都是些常见的米粮、豆类、蔬菜、菌菇,做法也强调清炖、蒸煮,少油少盐。
柳氏县主没有看那方子,她的目光依旧紧紧锁在林幺幺身上,仿佛在重新端量这个看似普通却处处透着不寻常的小村姑。
她当然知道不对劲,但是连宫里的御医都束手无策,这么多年了,心中的希望已经萎靡成一颗腐烂的种子。
“你方才所言……”柳氏县主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一种沉重的疲惫和挥之不去的疑虑,“那‘辛涩之气’,可能辨识出是何物?”
林幺幺心头一跳,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