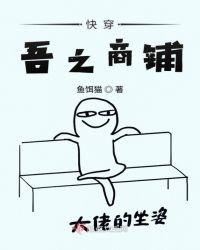02小说网>误惹檀郎 > 3040(第7页)
3040(第7页)
她又问:“那你二哥他,他还好么?”
时雪莹摇摇头:“二哥他也太冲动了,直接闯进知府官邸打人,巡抚已经勒停了他的官职。听说谢尚书大动肝火,还是太子出面承诺保他入阁,谢家才肯让这事作罢呢。二哥现在成日在家里待着,他心情很不好,谁也不敢去惹他。”
畹君心里一阵牵痛,好半天没说话。
时雪莹也轻轻叹了口气。
她和纪郎分离时都没这么消沉,可见革职给二哥的打击是多么大。要是有人陪他说会儿话,说不定还容易走出来一点。
想到这里,她殷切地对畹君道:“你找他有事么?我把他叫出来。”
畹君忙拦住她,轻轻摇头道:“不必了。我……没什么跟他说的。”
得知他并不安好,尽管那不是她想听到的答案,可到底还是达成了此行的目的,畹君知道自己该告辞了。
“三娘。”门边忽然传来一道紧涩的声线。
两个姑娘循声望过去,见一道高大的身影倚站在门边。
他穿着一身家常的玄色暗纹道袍,连网巾都没扎,几缕碎发垂在额前,显出几分不修边幅的落拓与失意。
时雪莹有些讶异:“二哥,你怎么出来了?”
“你先回去。”
尽管话是对着时雪莹说的,可他那双黑曜石般的眼睛一直凝视着畹君。
时雪莹不敢违抗兄长的命令,忙带着婢女回到了门内。
角门关上,廊檐下只剩相顾无言的两人。
冷阴的天色映在时璲的脸庞上,使那双乌浓的双眸更加深邃幽沉。
畹君错眼避开他的目光,却仍能感受到流连在她脸上的视线。
那视线是带着温度的,却不似以往的炽热。像熄了的火堆里的余热,眷恋尚存,却敌不过理智的降温。
半个多月前的依依惜别犹在眼前,那还是半黑的天,下着细雪。她被他半牵半搂着出了这道角门,他套马鞍的时候,她就躲在他怀里取暖。
可如今他们中间跨了一道鸿沟,谁也迈不出向前的那一步了。
畹君心里涌起千般情绪,追忆、不舍、难堪、心酸……乱麻似的一团堵在胸口,哪边也占不了上风。
时璲开口打破了沉默:“你……”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畹君抢在他前面说道,“你把我大哥害成那个样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时璲怔忪地望着她,眼里带着不容错识的愕然与沉痛。
畹君垂眸后退了一步,转身向街边停着的马车走去。
快到马车边上的时候,她几乎是小跑着,只想赶紧逃离这个境地。
车夫见到她过来,已经摆好了脚凳。
畹君踩着脚凳上马车,可是动作太急,牵扯到了她的腰伤,不慎整个人跌坐在地上。
身后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带起劲朔的风,吹得她发丝飘飞。畹君一手撑地,一手往身后一挡:“别过来!”
身后人的脚步声一顿。
她没有回头,咬牙扶着腰尝试着站起来,忽然整个人落进一个温暖有力的怀抱里。
那温暖也是稍纵即逝的,时璲将她抱起放在车厢前的横板上,便别过脸退开了一步。
畹君神色复杂地望他一眼,一言不发地钻进了车厢里。
“走吧。”她强压下声音里的颤抖,对外头的车夫说道。
“嗳。”
车夫应了一声,正欲扬鞭驾马,时璲忽然伸手抵住车轼:“等一下。”
他的动作带起一道劲风拂过车帘。透过被风拂起来的缝隙,畹君看到他骨节修长的手指攥在轼木上,连指尖都压出了褪色的白。
隔着一道车帘,他在外头轻声问道:“你……还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