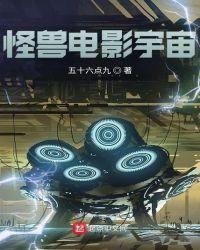02小说网>激流[刑侦] > 130140(第16页)
130140(第16页)
“他……手里有枪。”
在那夜钟楼会面之后,所有与“殉道者”有关的信息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牢牢按住了水面,连波纹都不许溅出。没有通报,没有新闻通稿,没有舆论高涨,甚至连警情公示栏上都只字未提“教堂”、“枪支”、“逃逸”。
而内部人都明白——上面早就知道是谁了。
在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这种诡异的沉默像瘟疫一样弥漫。许多民警心里都有数,却选择装作不知。有人私下嘀咕,说那人来头太大,可能和哪位常委挂了钩;也有人更敏锐,觉得这起案件已远远不是“杀人案”那么简单。
但不管怎么猜,大家嘴都很紧。
某天晚上,一位内勤民警偷偷向同事感叹:“你发现没?整个支队最近调取内部监控的视频申请都要上报市局……以前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那是因为上头怕我们看见那个名字。”
“哪个名字?”
对方只是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而时间继续向前推移,殉道者再没有出现。
似乎在钟楼一役之后,这场连环“供奉”彻底画上了句号。坊间流传的种种猜测——“自杀策动”、“制度复仇”——都像沙滩上的字,被潮水悄悄抹平。
望海市的节奏很快。媒体开始转向新的热点,学校恢复常规教学,公职系统开展作风整顿,一切都仿佛恢复了“正常”。
直到那天傍晚——
湾河西区某派出所门前来了一位奇怪的男人。他连滚带爬地跑进来,把手里的一封信交给民警。
那信笺的模样,民警们再熟悉不过。同样的信封,同样的纸张,同样的……殉道者。
殉道者又开始行动了。
而且,这封信是活人带来的。
第138章囚笼这次来信是想说明,我会引发一场……
那个男人坐在讯问室里,神情古怪。
灰色风衣的领子磨得起毛,袖口沾着泥点,裤脚湿了一圈,像是走过积水未干的老巷。他的头发贴在额上,一缕缕打着卷,像很久没洗过。脸色不算苍白,但皮肤下面的疲惫像石头一样钝重,埋得深。
最令人不安的是他的眼神。
他盯着地板,喃喃低语,声音一开始极轻,听不真切,后来逐渐急促,像被不断逼近的幻觉缠住:
“都死了……都死了……一个接一个……他们都死了……”
民警试图打断他,重复了三遍:
“你说什么?谁死了?”
他却好像听不到,一边摇头一边反复念:“都死了……都死了……该死的,不该死的……都死了……”
一名年长的民警皱着眉拍了拍桌面:“喂!你说清楚——谁让你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男人一愣,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像刚从梦游状态醒来。他眨了眨眼,忽然低笑了一声,沙哑又细碎,然后——又垂下眼帘,继续念:
“都是假的……假的……只有他是真的……他说得对,我们都在献祭……”
这番疯话听得人后背发凉。
“我觉得他精神不太对。”一个年轻民警小声说,“要不要先让人来评估?”
副所长摆了摆手:“先别急,支队那边已经在路上,等他们到了再说。”
“不过这人身上没伤,也没明显异常。他也不是戒毒反应,瞳孔正常。”
“封锁所有口径,一句都不许外泄。”副所长冷声道,“这封信绝对不能被任何第三人知道。”
应泊接到电话时正在单位帮书记员整理案卷,快到年底了,许多案卷需要归档。他一听完那头的话,就沉默地把案卷搁下,披上外套,转身下楼。手机还在耳边,却一句话也没说,只低声应了句:“我知道了。”
风从大门正面灌进来,他快步走向车库时正好撞见开完庭回来的侯万征。
“去哪儿?”侯万征一边摘领带一边迎上来。
应泊顿了半秒,只吐出三个字:“派出所。”
“……又来了?”侯万征眉心微皱。
应泊没多说什么,上了车自行离开。车开得很快,他握着方向盘,关掉了导航,顺便接了路从辜一起。路从辜斜靠在副驾,时不时瞥他一眼,应泊沉默良久最后还是开口:“这次信是怎么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