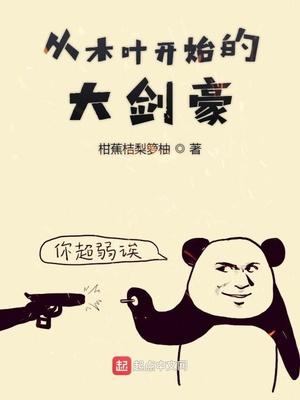02小说网>嫡嫁 > 3040(第25页)
3040(第25页)
慕莺时闻言,瞧着铜镜中纯美明艳的自己,不由得有些得意地抿唇笑笑。
抬手,抚了抚自己的鬓发,慕莺时弯唇笑道:“那是自然,我可比那个谢静仪小好几岁呢,而且,我的相貌本来便生得比她好看。”
对着铜镜中的自己,露出一抹有些得意的笑容,慕莺时自梳妆台的匣子中取出明修远给的房契与铺子凭证,对侍女吩咐道:“去将房契与凭证收好,过几日找账房过户。”
“是,奴婢晓得了。”
侍女接过慕莺时递过来的房契与铺子凭证,应声退下。
房间中只剩下慕莺时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她用檀梳慢慢地梳理着乌浓的长发,不晓得便这般过了多久,慕莺时站起身来。
走到窗前,想到了什么,慕莺时打开窗子,盯着正房的方向,眼中划过一抹带着冷意的寒光。
想到明老太太是为惠安郡主与明灿出头,方才会对自己横眉冷对,慕莺时暗暗咬了下牙,有些气不打一处来。
她眼底一片隐晦暗色,有些不忿道:“明灿,谢静仪,咱们走着瞧。”
……
“咳咳咳!”
坐在桌案前的绣墩上,明灿用帕子掩口,咳得眼前皆有些发黑。
咳了好半晌,垂眸,瞧见帕子上沾了一抹血丝,明灿有些无奈地抚了抚额头,迅速将手中帕子攥紧。
“小姐,药好了。”侍女用漆案端着热气腾腾的药碗进来,苦涩的草药味浓重。
瞧了一眼放在自己手边的药碗,已经喝了有一阵子汤药的明灿,不由得有些头疼。
自从上次在郊县老家落水之后,明灿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之前好不容易痊愈,没落什么太大的病根,但上个月,因为婚事心中郁结焦灼,不过在后花园散步,吹了一会子冷风,明灿便又感染了风寒。
这段时间,明灿一直在喝药,但却越喝越严重,每日早晨醒来,咳嗽得仿佛愈发厉害。
指腹轻抚着药碗细腻的瓷釉,想到了什么,明灿侧首,问道:“今日的药渣呢?”
听到明灿这般问,侍女想了想,忙道:“按小姐吩咐,皆留着了。”
明灿“嗯”了一声,然后瞧着侍立在身旁的侍女,吩咐道:“将药渣皆拿过来罢,我想瞧瞧。”
闻言,侍女应了一声,退下去拿这几日留下来的药渣。
待到将晾好的药渣拿过来,瞧着面前的几味草药,明灿用指腹轻轻拨弄着面前的药渣,却发现,几味熟悉的药材下,藏着些细小的褐色碎片。
微皱了下眉,觉察到了什么,明灿对一旁侍立的侍女道:“去请周婆婆过来,便说我要绣个新花样。”
周婆婆很快便过来了。
明灿将放在桌案上的药渣推到周婆婆手边,只见周婆婆站在明灿身旁,垂首用指腹拨弄着药渣,半晌未曾言语,仿佛是在思忖着什么。
许久后,辨认得差不多的周婆婆方才对明灿曲膝礼了礼,回禀道:“小姐,这里面桔梗放多了,而且还加了杏仁……这哪是治咳,分明是要教小姐咳得更厉害!”
听到面前的周婆婆这般说,明灿不由得心中一颤。
抬眸,定定地瞧着站在面前的周婆婆,明灿问道:“可以确定吗?”
周婆婆闻言,面色有些不好看地点头,回答道:“千真万确,老婆子娘家是郎中,自药铺做了十多年工,绝不会看走眼。”
说着,想到了什么,周婆婆有些气愤地对明灿道:“这药再喝下去,肺皆要咳坏了,小姐快些停药罢。”
听罢周婆婆的一番话,明灿沉默了下去,手指轻轻地敲着桌案,不晓得在想些什么。
好半晌,明灿命一旁的侍女将桌案上的药渣收进荷包,然后抬眸,瞧着周婆婆道:“这件事,还请婆婆且先保密,莫要告诉任何人。”
听到明灿这般说,周婆婆忙点头不迭。
“奴婢晓得。”
静静地颔了下首,明灿命周婆婆退下。
在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明灿不想打草惊蛇。
虽然,这种下三滥的阴私狠毒手段,明灿大概已经猜出是谁干的了。
但,在拿到证据之前,明灿决定将这件事,暂时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