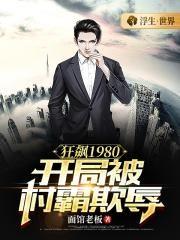02小说网>鸣珂 > 第193章(第2页)
第193章(第2页)
徒弟见他从廊下来,恭敬地从耳房里捧出早备好的参茶递上去,低声道:“师父,今日世子回京,刚递了折子上来,陛下正看呢。”
盛江海道声知道了,端着参茶轻轻地进了屋。檀木绣花屏风之后,奏折整整齐齐地摞着放在书桌一侧,皇上手里擎着一支紫毫,一幅字写到末尾,就快要写完了。
他听见屋门响动,也没抬头,问道:“临徵他们已经进城了?”
“是,”盛江海把参茶放在他手边上,小心地拿远了些,免得挥毫时碰了,“傅行州同他一起,上午就进城了。把杨淮英两人送到御史台去押着,您也派人传了旨说不必今日觐见。他们两人就回府了,其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
皇上嗯了一声,不明喜怒,拎着笔瞟了一眼那参茶,忽而问:“盛江海,你跟着朕,多少年了?”
盛江海手中一顿。他刚刚进屋便觉得气氛不对,应答也是十二分地谨慎着。既然问起了便是意有所指,只是不知道这折子上说了什么,引得他如此疑心。盛江海双手依然捧着盘子,趋步后退两步,笑道:“回陛下,奴才自幼进府跟随您,已是四十二年又八个月。”
“你进府时正值冬天。朕记得,当年先废太子府查抄时也是冬天。”皇上指尖捏着笔,向他偏过头来,神情冷峻地审视着他,“抄检是你主持的,当时可有什么遗漏吗?”
盛江海心中悚然般一震,但面上丝毫不露,快步退后跪到书桌前方回话:“回陛下,当年查抄一应物品、家财金银,都全部收悉登记至刑部,每件物品收检后皆由三人以上核查比对,并无缺漏。臣斗胆问一句,陛下忽然查问此事,可是少了什么?”
“那人呢?”皇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目光沉重而冰冷,似有千钧之重,“抄检时衡国公也在场。他可有藏私或者偏袒先废太子之处?他会不会有什么心思,会在背地里偷偷授意给萧临徵?”
“陛下,”盛江海直身跪着,双手拢在袖中,向上高高地一拱手,铿锵地说,“当年不但衡国公阎珩在场,漓王殿下也在。我们三人一应言语行动皆有刑部实录,臣可在此以人头性命发誓,绝无半句僭越之辞!臣微贱不值一提,可漓王殿下是何等人品,对陛下是何种情谊,天地之间唯陛下心中明鉴。即便人人皆有私心,漓王殿下也绝不会有!”
他说罢,皇上未置一辞,只是指节用力地拗着笔,目光沉沉的落下来,像利剑一样几乎要把他穿透了。书房里一片寂静,只听得窗外翻滚不止的雷声。
盛江海胸腔里的心跳声与更漏声混在一起,就这样直挺挺地跪着不知道等了多久,才见皇上把笔一放,向侧摸过翡翠珠哗啦哗啦地捻起来:“行了,起来吧。多大点事,看把你给吓的。”
盛江海道了声谢陛下,心中疑虑不减。他起身缓步回到桌旁侍立,见皇上拿了参茶要喝,上前道:“茶放凉了,只怕失了药性,陛下还是别用了。外头备了新的,臣这就去拿进来。”
“无妨,”皇上向他摆了摆手,拿起茶盅来喝了一大口,又把一封奏折从旁边捡出来,随手扔给他,“老三刚到兖州,折子就跟着来了,你自己看。”
盛江海打开一目十行地扫过,看罢震惊不已。萧临彻上书称先废太子有一私生子藏在兖州,指控衡国公当年有意留其性命。阎止此去兖州,正是要帮助此人逃窜。萧临彻在奏折末尾询问,若是抓到了可否先斩后奏,见机行事?
“瑞王此言空穴来风,毫无凭据,”盛江海皱眉,难得肃容道,“陛下,即便真有此事,该问的人也是闻侯。当时闻侯不在京城,衡国公与漓王只是奉旨去府中抄检,如何能够藏人?但瑞王所请先斩后奏,他若不清不楚地拎着个人头回来定了罪,于朝中怎么论断,于闻侯又怎么论处?”
“朕知道了。”皇上说罢,执起笔来接着写,又道,“如果杨淮英包庇先废太子后人,朕必杀之无疑。”
盛江海走上前去,在侧研墨。他手下还没画两圈,皇上忽而拿过个金蟾抛给他:“好了,今天也没有什么要紧事,早点回去歇着吧,让你徒弟来伺候就行了。”
盛江海握着金蟾谢了恩,又听他说:“临徵此番案子查的不错,病没见好又舟车劳顿,不容易。你去按瑞王之前回京时的礼单,替朕赏一份下去。”
夜色漆黑如墨,平王府卧房的廊下还亮灯。阎止从黎越峥手里接过药,又听了两箩筐的嘱咐,这才回身进门。
屋里只点着床前的一盏小灯,四下都是暗暗的。萧翊清散着头发靠在床头看书,见他回来,语气里带着嗔意:“大半夜的怎么还过来了。怕人看见,还要从后门偷偷地进来。”
阎止把药递给他,再把勺子转到他手边去,顺势在他床边坐下:“我要是不来,你们两个人拌嘴,一个不吃药一个不睡觉,这日子还怎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