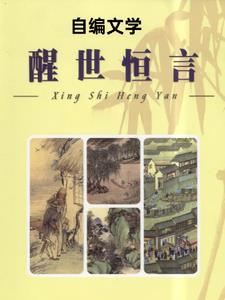02小说网>帝台困娇 > 7080(第14页)
7080(第14页)
李太医休养多日终于能下床,他带着小徒弟一起来长明宫,小徒弟正是之前在马车上替江念棠把脉的张太医。
张太医不仅是李太医的徒弟,也是他挚友的独子,之前张太医被陛下嫌弃的事儿传到李太医耳朵里,他就在琢磨着如何帮徒弟重新立名。
李太医已经到了荣养归乡的年纪,心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张太医,如果陛下对他的印象停留在医术不精,往后他在宫里的日子就会很难熬。
因而今日他把张太医叫来打下手,希望能在陛下和皇后面前挽回一些印象。
张太医明白师父的苦心,心里感激不尽,动作愈发谨慎,生怕出错。
“昨夜她腹痛如绞,缘何如此?”赵明斐坐在一旁,无形中散发的威压令张太医背脊生硬。
李太医是赵明斐的心腹,亦是看着他长大的人,说话不像其他太医那般隐晦:“臣观娘娘面色苍白,脉象虚弱,体虚之症愈发严重。”
他眉头一皱,狐疑地再次搭三指诊脉,闭目细细感受。
屋内陡然寂静下来,只听得见些微的呼吸声。
赵明斐亦安静等候,无声瞥了眼榻上的江念棠,眉目微冷。她面色如常,好像对自己的病情一点也不关心。
李太医一直屏气凝神诊了近一刻钟,方才睁眼,面色似有犹豫。
赵明斐道:“太医不妨直说,这里都是自己人。”
李太医捋了捋下颌胡须,沉吟开口:“臣斗胆,娘娘似乎是……中毒了。”
话音一落,满室皆惊。
赵明斐周身气势陡然上升,眸光锐利如刃尖扫过在场每一个人:“中毒?”
被扫射的每一个人无不惶惶瑟瑟跪下,其中右想感受到的压迫感最大,她负责长明宫里里外外所有事物,江念棠衣食住行皆经她手。若说下毒,她是最有机会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
右想当即激动地跪着指天发誓:“奴婢素日里谨慎小心,但凡娘娘接触之物无一不亲力亲为,尤其是入口之物更是慎之又慎,请陛下明鉴。”
说完她伏地而跪,不再辩驳。
赵明斐冷厉的目光扫了一圈,他也不信有人敢在长明宫下毒,眸光明明灭灭最后落在江念棠身上。
江念棠没想到来了个医术精湛且真敢说的。
她敢用朱砂避孕就是在赌太医院们没一个能想到,就算是想到也不敢说,况且她这段时间已经停用朱砂,还想方设法排出体外,理应无碍。
本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杀出个程咬金,她此刻只能装到底,更没想到赵明斐居然如此敏锐,第一个怀疑到她身上。
毕竟自己下毒害自己一说实在太过匪夷所思。
江念棠佯装皱眉不解,眼神还有几分惶恐茫然。
赵明斐眯着眼凌厉地审视江念棠,沉声问李太医:“能诊出是什么毒吗?”
李太医摇摇头:“陛下稍安勿躁,娘娘体内毒性不大,于身体暂时无碍。只是一时半刻不好确认,需要仔细问过娘娘平日里的衣食住行才能准确判断。”
他转头看向右想,“皇后娘娘近半月的一日三餐,还有所有入口之物你且说来与我听。”
江念棠身为皇后,一日三餐皆有详细记录,包括吃了什么菜,吃了几口,吃后反应等等。
右想亲自去取了她的起居注,在李太医翻阅时静默不语,他稍有疑问立刻回答,无一不细。
李太医不消多时便翻阅完毕,随手递给张太医复核,自己又问起皇后平日里接触的东西。
右想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遇到可疑的物件立刻叫人搬来让李太医查验,但均一无所获。
江念棠提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料想是体内朱砂毒性太弱,无法被诊出,只要她咬死不认,没人能查出来。
赵明斐的注意力一直放了一半在江念棠身上,她从眉目紧绷到松动之态被他尽收眼底,眸底不由渗出几分阴沉。
他敢断定,她身上的毒十有八九与她自个儿脱不了干系,只是赵明斐没想明白她为什么要给自己下毒,而且这毒不影响平日生活。
现在没有证据,赵明斐先按兵不动,等李太医查出是什么东西后再好好跟她算账。
李太医皱眉沉思,再问:“皇后娘娘平日里有什么爱好,亦或者近日有什么变化?”
右想又一一细说,李太医细细琢磨后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然而跪在李太医旁边一直充当木桩子的张太医神色古怪,他偷偷抬头看了眼榻上的江念棠,只见她一副面容淡漠的模样,欲言又止。
赵明斐何其敏锐,当下厉喝一声:“张太医有话直说,若敢隐瞒乃是欺君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