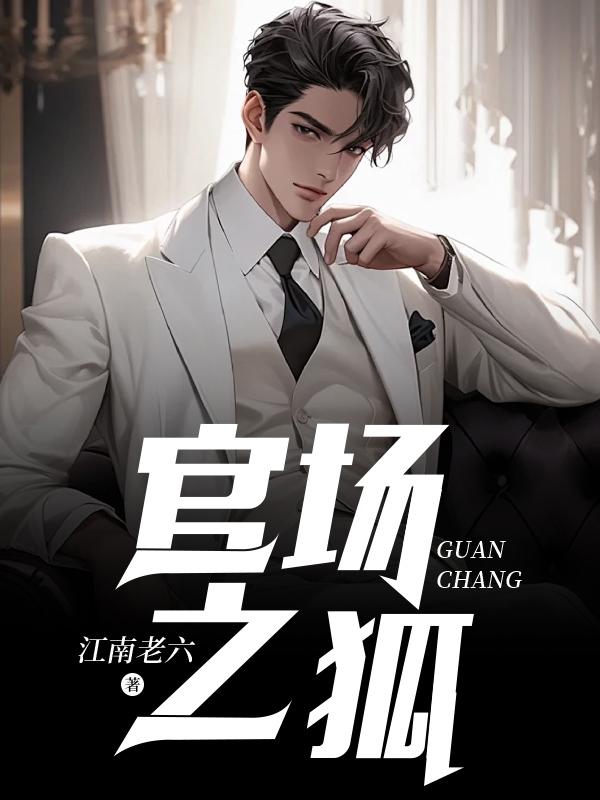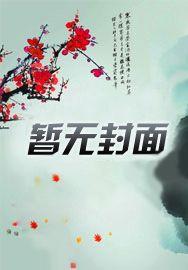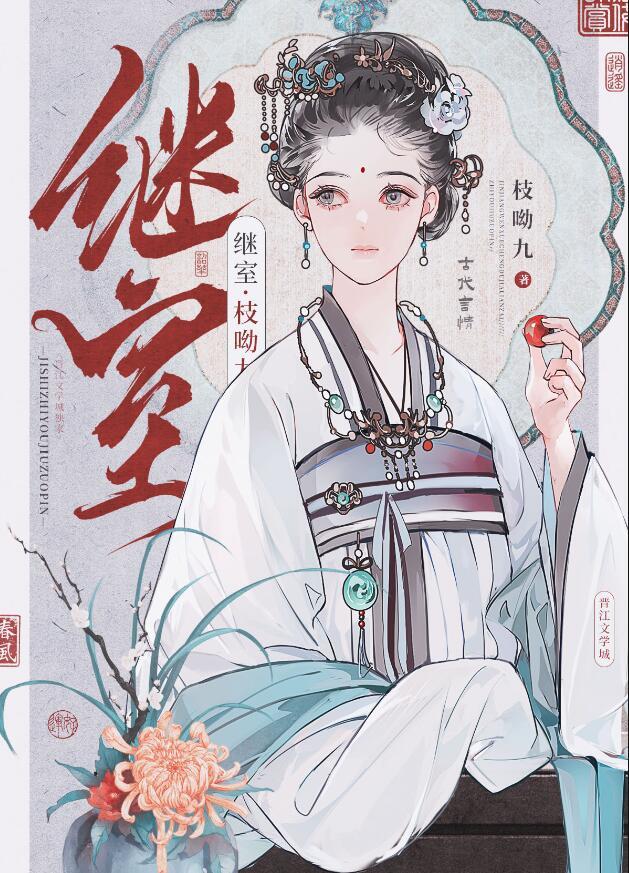02小说网>韬略 > 5060(第27页)
5060(第27页)
尚书令,乃前朝旧制,位同副相。
大司农程勉之道:“陛下,臣有异议。”
“臣若是没记错,前朝废除尚书令一职,正是因为尚书台与宰相府职权重叠,易致于政令多出,朝臣相互倾轧,恐怕因此而多生事端,还望陛下明鉴!”
殿内不少人纷纷附和。
“程大人此言差矣,尚书台不过是协理政务罢了,何必危言耸听?”宋百鸿慢悠悠道:“增设几位尚书令,既可以示陛下体恤臣子之心,又能替萧相分忧,实为利国利民之事。”
程勉之神色一冷,他高声道:“陛下!宋中丞此议有离间君臣之嫌,臣请治宋百鸿妄言之罪!”
话音一落,宋百鸿神色有片刻的慌张,他匆忙瞥向龙椅上的赵从煊,很快便又移开了眼神,神色稍定,“臣不过是为国献策,何来离间之说,程大人是要堵塞言路?”
朝堂顿时分为两派,争吵愈烈。
萧伯瑀缓缓抬眸,正对上御座之上,年轻帝王的目光。
赵从煊的眼神很静,像一泓深潭,不起波澜,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萧相以为如何?”赵从煊道。
以萧氏的威望、萧伯瑀的权势,倘若他反对,即便宋百鸿再说些什么也无济于事。
可萧伯瑀只是看着座上之人,直至眸光暗了下来,他躬身出列,沉声道:“臣附议。”
话落,周遭一片愕然,程勉之失声道:“萧大人”
尚书令一旦落实,宰相府的势力分割,到时又是一场党派争斗。
萧伯瑀却像是没听见,他继续道:“陛下圣明,臣附议宋中丞之请。增设尚书令,确能分忧解劳,臣愿以国事为重,不负陛下厚望。”
朝堂之上,众人神色各异。
程勉之眉头紧蹙,宋百鸿则难掩喜色。
龙椅上的赵从煊,紧紧地看向萧伯瑀,手指微微收紧,良久,他才道:“准奏。”
退朝后,萧伯瑀独自走在宫道上。
“萧大人。”身后传来程勉之急切的声音,“您为何要答应此事?尚书台一旦设立,宰相府必将——”
“程大人。”萧伯瑀打断他,声音平静道:“陛下既已经下旨,我等照做便是。”
程勉之一怔,随即明白了什么,脸色煞白:“难道这是陛下的意思?陛下怎么会——”
“慎言。”萧伯瑀继续往前走着,轻声道:“为官者,上不负君主,下不负百姓,便足矣。”
尚书台的设立,极大地削弱了宰相府的政权。
不过,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每逢休沐日,萧伯瑀甚至有时间摆弄起后院的花草。
院内,有一株兰花开得正好。
萧伯瑀将它挪到书房窗台,抬眸间,正对上书房内悬挂的那幅墨兰图。
他回想着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眸间陷入了深思。
调任萧氏朝臣时,萧伯瑀没有为他们求情,分化相府政权时,他也没有为自己据理力争。
他所做的一切,全然顺从圣意。
这样,够了吗
“陛下”萧伯瑀轻声低喃,良久,他低下头,嘴角勾出苦涩的笑意。
九月,西北传回军报。
这仗还没开始打,“北晟”的新君王便送来和解书,声称从前是代王赵铎年迈昏聩,一时糊涂才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愿陛下看在同为赵氏子弟的份上,宽宏大量
朝中之人对此,意见不合。
有人认为,“北晟”政权的建立本身就是对大晟国威的挑衅,应当论谋逆之罪处置。
也有人认为,赵铎已经死了,其子孙愿归顺大晟,何不顺承其意,这样也能免了干戈,百姓也免于涂炭。
萧伯瑀入宫进谏:“北晟之事,臣以为,陛下当以‘怀柔远人,敦睦宗亲’为本。赵铎虽僭越称帝,然其孙既愿奉表称臣,若严加惩处,反失四方归化之心。不若赐其侯爵之位,以示陛下宽仁。再者,战事一起,生灵涂炭,还望陛下三思。”
一字一句,尽其臣子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