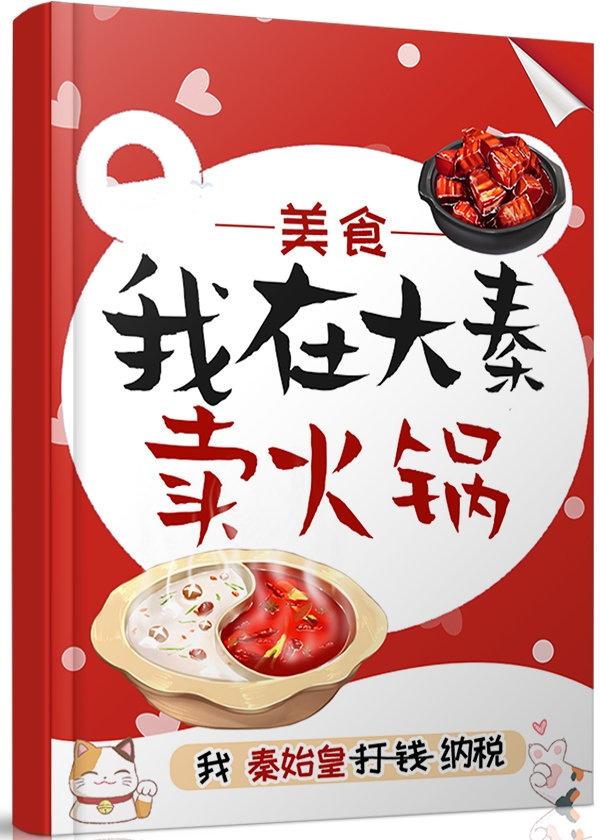02小说网>荷花今日复仇否? > 王府(第2页)
王府(第2页)
但这这一切皆太过顺利,司衣荷心中隐隐有些不安,无论是卫夫人亦或是卫清评的书信,好似都透着些蹊跷。
不多时,三人便已稳稳停至王府门前。
这王昌荣不虚为青州首富,这王府门庭巍峨,金匾朱门,单是这门头的气派便就不是卫府可比,可这王府门前,竟无一人看守。
他们面面相觑,皆在对方眼中瞧见了惊疑:偌大王府,门前竟空无一人,连个应门的仆役也无,竟空荡至此。
燕扶青上前欲推开那沉重的朱门:“怪事,此前来王府,并非这番光景。”
司衣荷急着寻映香,她脱口道:“世子殿下,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先进去探看吧。”
“好。”
燕扶青掌心发力,将那府门推开,待看清门内景象,他们俱是一惊,只见庭院里头狼藉遍地,箱笼翻倒,绫罗绸缎与金银珠宝散落一地。
庭中却不见侍卫婢女,唯有卫平生一人,孤影孑立于庭中,他背对着司衣荷三人,手里还握着那把与燕扶青打斗过的长剑,剑端低垂,滴滴鲜血砸在了这狼藉之上。
司衣荷心头狂跳,她踱步上前,直视卫平生:“你做了什么?”
卫平生脸上溅着几滴血,目若空洞,苦笑着道:“杀人了。”
杀人了,他就这般轻巧道出。
燕扶青唤来白纪将卫平生押着,卫平生毫无反抗,任由白纪将他钳制住,那柄长剑哐当着地。
他对着司衣荷道:“我们先进去探看究竟,再下定论。”
他们循着那道尚未干涸的血迹,最终停在了一处书房前,血迹却似被凭空斩断,止于一处封死的墙壁前,既玉迅速俯下身,指尖撇了一点血迹凑近鼻端细闻:“这确是人血,气味浓烈,只怕有暗道。”
欲问那卫平生,他却只低垂着脑袋,充耳未闻,司衣荷心急如焚,只好摸索着。
她素手摸过每一处墙壁、每一处雕花,终在一卷书籍下寻到暗道机关。
暗道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燕扶青寻了盏灯提在手中,晕开一丝光亮,他侧身将两人护在身后,轻声道:“你们二人,莫要离我太远。”
三人循迹往前,步步深入,却见豁然开朗,昏黄的灯光映出一处不大的暗室,往前一看,映香被粗绳捆绑着丢在那里,口中紧紧地塞着布巾。
她浑身颤抖,待看清来人,惊恐地睁大双眼,哑声哭着。
在她身旁的不远处,一张玉石桌上,王昌荣头颅歪向一边,嘴巴张着,嘴角溢出一道黑血,双目圆睁,已然毫无生气!
司衣荷上前,小心翼翼地解开映香身上的粗绳,她动作极轻,又轻柔地取下塞在映香口中的布巾。
映香脱了禁锢,便直直地倒着司衣荷,死死地抱住她,劫后余生的恐惧与委屈交织在一起。
她小脸苍白,哭喊着:“姑娘,姑娘,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原先在舫前守着摊子,忽然眼前一黑便到这里了!那王昌荣本欲对我行不轨之举,可我不知怎的又昏了过去,醒来便瞧见他倒在哪里!”
司衣荷眼中盈着泪,轻抚着映香的背,她压着喉间的哽咽,柔声道:“都是我不好,莫怕,我带你回家,带你回家。”
与此同时,既玉同燕扶青早已上前查探王昌荣的尸体,既玉神色微凛,确认王昌荣了无气息,又端起他手边的那杯酒。
既玉惊呼:“这酒中有毒,王昌荣并非中剑身亡。”
燕扶青拧眉问:“何以见得?”
既玉缓缓将酒杯放下,解释道:“这毒气味辛烈如腐骨,名唤见狱,只消一口,便足以当场毙命。再看这王昌荣唇色紫黑显现血斑,便是见狱之毒的症状,而这胸口剑伤,离心脏尚有三寸之余,且从血渍看来,色泽鲜艳仍带温热,明显不过片刻前新添。这王昌荣分明死于酒中之毒,而非卫平生剑下!”
“只是我想不明白的是,”既玉顿了顿,又继续说道,“这毒药价格不菲,气味明显,绝非寻常人家可得。纵然酒香馥郁,也定然掩盖不住这毒药气味。他王昌荣,为何要饮下这杯毒气四溢的酒?还有那卫平生,为何要在他死后刺他一剑?”
司衣荷听着这番分析,手中安抚映香不断,接话道:“王昌荣定不可能了断自己,若非自愿,定有人胁迫亦或哄骗他喝下。至于卫平生,恐在掩盖些什么。”
闻及此,映香怯怯开口:“姑娘,我昏迷之时,除却王昌荣的声音,好似隐隐约约听见了另外一个男子的声音,听起来约莫跟司伯那般大。”
男子?
燕扶青暗暗思索,再往里走了一点,细细打量着四周,却见角落里有一块粗布,紧紧地掩盖着处小丘般高的东西,他走过去挑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直刺鼻尖,再定睛一看!里头竟歪歪斜斜地躺着七八具少女尸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