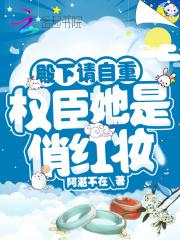02小说网>[民国]那年我妈离婚未遂后 > 灰龙执绋(第3页)
灰龙执绋(第3页)
王遗时在餐桌前坐下,惜予让张婶给他盛了饭来。
“知道你喜欢,宁宁都没吃几口鱼肉,要给你留着。”
王遗时看了眼几乎完好的鲈鱼,叹道:“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气。”
“我想你是知道的,只是不想承认理由吧。”惜予靠在桌边与他说。
“你就别戳穿这层薄薄的遮羞纸了,”王遗时说,“园丁天天浇水修枝,奈何花不开叶不绿。也是奇了怪了,我每次问她‘懂了没’,都说‘懂了’,原来是假懂。”
“宁宁心思重,怕问多了你会生气,会对她失望,她不敢问。”惜予又说起自己读书时后来居上的故事,让他宽心,且多给宁宜一点时间。
事后张婶和惜予感慨:“公寓的太太们背地里喊你‘甩手掌柜’,我看,在这个家,把你劈成两半都不够用的。”
—·—
惜予和王遗时正在育儿风波中载沉载浮之际,残酷的噩耗突发而至,管家恩挺赶来上海报丧。
1935年6月4日,安安因产后羊水栓塞引起大出血,抢救不及,不幸离世了。而婴儿在腹中呼吸受阻,落地后,一声啼哭也未曾有,便也终结了她与这人世短暂的缘分。
惜予夫妻与慎予同一时间得知消息。夫妻俩次日赶回杭州老家,而慎予更先一步,连夜驱车回乡。
谢家老宅前厅已设灵堂,正中央摆着一张安安遗照,笑容恬静。安安就睡在后面由雪白雏菊环拥的棺柩里,她曾经时多么鲜活的一个女孩,羞涩的、欢喜的、忧郁的、平静的……如今面容上已分辨不出任何情绪。
没有人敢于设想,她离世之前遭受了多么锥心刺骨的痛苦。
慎予紧紧靠着棺柩,就像往日安安依偎在他身边时那样,一遍又一遍抚摸她的脸颊。
惜予走近前,一见到棺柩里离人旧貌,便掩嘴恸哭,王遗时不断抚摸她的背脊,以旁人听不见的低声呢喃:“别哭,别哭。”
慎予半跪着,最后一遍伸手抚过安安脸颊,捡去一根贴在她脸颊边的断发,专心把目光投掷在妻子身上。
“安安,你一直在等待我、成全我,这些年我只知接受,从未设身处地为你想想。是我对不住你,都是我不好。”
灵前的深情,死后的道歉,何其卑贱无用。可他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而安安又何曾怨怪过他呢?
停灵结束以后,封棺落葬,大小两具黑漆杉木棺材就此紧密相依于孤山松声竹涛之间。
慎予与安安青梅竹马,好容易做成了夫妻,又盼得苦尽甘来,谁知一朝阴阳相隔。一生一世的美好展望与无数承诺自此随着黄土,被掩盖在不见天日的幽冷地穴中。何止他二人,世间多少海誓山盟都败给了死亡。
从族墓回去路上,路经钱塘江畔,慎予停了下来,往江面上眺去。
此日潮汐不兴,澄江如练,慎予想起旧日与安安一同挤在人群中观大潮的经历,年年如此,止于今岁。
“我要离开杭州。”他对惜予说,也是对安安说。
—·—
回上海的火车上,惜予一直没有说话,王遗时也安安静静,望着车窗不断倒退的山野、城郭出了神。
惜予突然唤他,“善言,你去吧。”
没头没尾的一句话话,王遗时问她:“你要我去哪?”
“去完成未竟的学业。”
王遗时骤然从座垫上起身,起至一半,又坐了回去。他叹道:“是我自己放弃的,怎么突然又提这事?”
惜予兀自看着窗外,青绿原野在眼前飞掠成模糊一行,天边阴云绵延数里,浩浩无边,好似一条执绋送亡的灰色长龙。
“这几年,你一直在向我赎罪,”惜予转过头,遗时仍然注视着她,“已经够了。现在我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眼下世道乱糟糟的,我王遗时虽非参天巨树,可即便是片莲叶,也想守护叶底一荫安眠。我远游求学去了,你带着两个孩子,太辛苦了。”
惜予听他脑筋一时不肯转弯,便暂且将此事按下了。
回到上海后,又数次劝说,王遗时逐渐动摇,最后在惜予鼎力支持下,辞去大学工作,是年冬天将赴德国亚琛深造。
在他以前,慎予先一步北上求学。
他这年从医学院毕业后,不管工作还是继续读书,慎予只知道自己绝不会再待在沪、杭两地。谢老爷体谅他睹物思人,索性放手支持,只在地点上稍作要求。
因谢老爷厌烦洋人,出国自然不可行。王先生便建议谢老爷送慎予去香港,说那边认得熟人,可以帮忙照顾。可谢家大哥便是留学香港,最后死在了广州,谢老爷提起来便长吁短叹,哪敢再送一个孩子过去。
选来择去,最终定在北平,幸亏他成绩优秀,得以被清华录取。
临行前,慎予将女儿瑀舟托付给谢太太抚养,只身踏上前往北方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