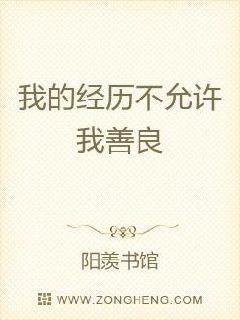02小说网>金枝 > 3040(第21页)
3040(第21页)
但捕风捉影的事,全凭听的人愿不愿意当真。祁无忧不信,他说再多都是噪音。
濯雪端茶进来时,说晏、李还没走到大门,也为着这事不欢而散了。祁无忧凝神一想,暗骂夏鹤真是个祸水,才几天就给她身边的关系带来了接连麻烦。
“那祸水人呢?”
“谁是祸水,我吗?”
落地的窗板支了起来,夏鹤踏着外面的明媚秋景走进屋里,像画框中走出来的仙君。
祁无忧警觉:“你何时来的?难不成在偷听?”
夏鹤“哦”了一声,似有所悟:“看来那两个人是来搬弄是非,说我坏话的。”
“什么搬弄是非、说你坏话。”祁无忧脸不红心不跳,“你可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不爱听你说长倩的坏话。”
“我不信他没说过我的坏话,你爱听吗?”
祁无忧被问了个正着。
何止爱听,她甚至还附和过呢。
夏鹤见她不答,心中有数。他点到为止,没有穷追猛打。时日久了,她自会慢慢意识到坏话也能中听,她待他又有多少不公平。
他坐下,随口问了句:“你跟李定安也是青梅竹马?”
祁无忧见他主动转移话题,便有什么说什么,包括他是她在军中的耳目也一并说了。
“你打听这个,不会是想找机会挑拨离间吧?”
祁无忧是开玩笑,但夏鹤却没有否认:“他不值得你这么重视。”
他曾跟李定安打过交道。
当时他还是夏在渊。他们与梁军隔江对峙,他做先锋,李定安从后面包抄,约定在关口会师。但李定安贪生怕死,又因自己据守的主张被驳,很没面子,所以出尔反尔,没有出现。
夏鹤那回九死一生,三千人去,三千棺归。虽打了胜仗,营地里却漫天素缟。
他无法对祁无忧讲述这段故事,否则身世就会败露。
她问“为什么”,他倾身靠近些许,低沉清晰的私语缓缓淌入耳中:“其实你很清楚,李定安只是个纨绔。但你手里的牌只有这么几张,所以再烂也得硬着头皮打下去。”
祁无忧心一颤。
她凝目望去,夏鹤神态自若,肩上承着一层秋日洒下的金光,衬得他这个人愈发玄妙起来。
但祸水不能凭自己天生丽质就肆言无忌。
“我才刚许你回来,你就挑唆、进谗?”祁无忧恼他贼心不死,故态复萌,说这谗言进献得真没水平。
“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觉得是谗言?”
“你怎么不想想,我和他们认识多久,又跟你认识多久?你了解我多少,我又了解你多少。他能帮我带兵,帮我在军中笼络人心,你呢?疏不间亲,我凭什么听你的?”
夏鹤一听,谁疏谁亲,她倒是分得挺明白。
不过上次他连一个纪凤均的分量比不过,这次就更没有必要争长论短。
祁无忧扬眉等着他回嘴,他却出乎她的意料,耐着性子说:“好,那从今日开始,我只说‘殿下你美若天仙,令我心心念念,浮想联翩’,你听不听?”
青年的嗓音娓娓动听,清俊朗润的眼睛又不掩饰款款深情。祁无忧顷刻顿滞,转瞬又伶俐起来:“你唱戏呢。行啊,你说啊。就说你怎么想、怎么念、怎么联翩!”
她理了理宽大的衣袖,做出洗耳恭听状,谅他没读过几本书,做不到晏青那样出口成章。
但夏鹤总是不遂她的意。
他牵住她扬起的衣袖,手臂又伸了伸,将人拉到腿上坐下。这些日子躬行实践多了,夏鹤对如何与妻子亲昵已得心应手。
祁无忧乜斜。谪仙模样的男人原形毕露之后,不过是区区色鬼□□。她且看夏鹤是把他的“浮想联翩”付诸行动,还是肚子里的墨水不够了,不动手动脚就表达不出来。
但未曾想,夏鹤微微仰头望着她,眼底湛清温热。
此情此景,就是定下山盟海誓也顺理成章。
他伸手拨开她鬓边散乱的步摇金穗,替她别在耳后,说:“李定安会做的事,我能做得比他更好。”
祁无忧低着眉眼凝视了他许久,莫名心神激荡,怦然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