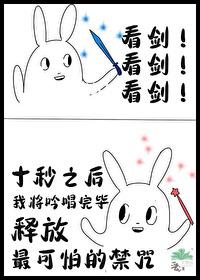02小说网>奔跑着 > 滇朴(第2页)
滇朴(第2页)
她也一眼命中自己的故事真相,背对着聂医生坐下。
聂尘炀取下眼镜,“37dB,不是什么大事,你多久没有做过检查了?”
杨桉旋转自己的脚尖,满不在乎地回忆,“我看看啊!5、6年了吧,最后一次是32dB好像,但是这个波动太小,而且临床的影响因素过多,就没在乎了。”
聂尘炀点点头,“确实,看你的状态也不错,但是我害怕你的晕眩症状加重,毕竟它一直这么响着,什么玩意都有一个使用年限、频率、次数,就怕万一那天卡壳了,或者接触不良。”
随即起身做到杨桉一侧,继续和她分析,“下个月再来检查一次,我再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波动,是不是你这几个月工作太狠了。”
“好。”
“怕吗?”
杨桉摇头,直面着聂医生,“我接受自己的左耳10年了,要不是因为听不太清晰或者有回响,让我一直有种错觉,它只是坏了,也不是全坏,不然我都会怀疑我听到的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它就像是一道疤,完全愈合了,只是还有色素沉积:一个外涉入的器材,完全可以正常行事,但是就长得不一样……”
“换言之,我只要一直生活,这问题会和声音一起回馈给我,我会接受,而且也只能接受。不是有句话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旧会仁爱生活。’欸,谁说的来着?”
聂尘炀看到如此豁达的杨桉,笑了一下,“是罗曼。罗兰。那我就不担心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了解一下助听器,手语会吗?”她身上有远超常人的安定。
杨桉:“确实可以了解,接触这些也不难,手语的话,大学的时候选修过,也做过志愿者和义工,略懂皮毛。”
杨桉和聂尘炀道完谢意,走上下往一楼的电梯,直到看不见头了,聂尘炀才对着走廊另一边说:“出来吧!”
转头看向他,差点惊掉下巴,“哪里来的口罩?”
谢树低头失笑,刚刚一上去,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他,谢树以为发生了什么,左曦指着他的口罩,“你要不要去照照镜子?”
整个口罩是上半部是水色,下半部的视觉盲区是淡粉色,杨桉还在上面贴了几个可爱的蝴蝶和草莓贴纸,女生带着不会奇怪,但他一个冷面脸,走起路来只会双手插兜、目中无人,还通常只穿一身黑,那那那都看着不相称,十分别扭。
像是强装可爱的硬汉。
聂尘炀倒是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维持自己的嘲笑,问他“她不想让你知道?”
“应该是。”
“有什么打算。”
谢树没说话,看着杨桉站在庭院里和小朋友打招呼,然后又从她的百宝箱一样的包里,掏出一大把糖给小孩,碎阳暖暖地打在绚烂的糖果上。
和小孩告别后,杨桉掏出手机,谢树看了一眼自己的,“聂叔,我先走了。”
“你在哪?”
“你身后。”
杨桉转了一圈,透过来往的人群找到了谢树,于是跳起来挥手,谢树笑了一笑,向她跑过去。
二楼的聂尘炀插兜在白大褂里,看着阳光下的他们汇合,顿时觉得这夏日的庭院更加生机盎然,“多好的两个人啊。”
州医院门口的蓝花楹道,落英缤纷,蓝色的花朵似鹅绒散落一地。
杨桉看呆了。
谢树正在远处等着司机把车开过来,满树花海里的蓝天澄澈清透,风吹着盛夏的躁动,轻拂起他额前的短发,杨桉不由自主地按下快门。
插兜的、挥手的、回头看她的、单独的背影,她想起自己被他偷拍的那张照片,不说姓名,不知道是谁的隐秘感,会让人止不住遐想。
路沿石和沥青路面的排水口下,干枯的花瓣和刚刚飘落的花朵鱼龙混杂,她蹲在地上往下拍,斑驳的地面被放大,花朵上筋脉别样妖艳魅惑……
谢树过来时,她还在很投入,“走了。”
“马上就好。”
杨桉视线一抬,看着地面上的影子落在场景中,为纯净曝光的照片增添了一角的阴影,画面被灰暗色块分隔,“别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