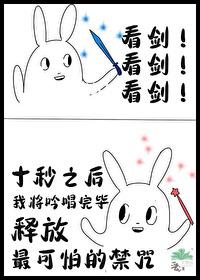02小说网>奔跑着 > 滇朴(第1页)
滇朴(第1页)
输液大厅人满为患,杨桉戴好口罩,盯着窗边的一个阿姨正在收拾行李,旁边的小学生摁着手背。她若无其事地悄悄走过去,装作看风景。
谢树缴费完,找到她,“等个10分钟左右,真的不用去病床上躺着?”
杨桉掏兜摇头,“不用,就两袋,很快的,而且昨晚睡得好。”
拍拍凳子,“来,坐下。”
谢树不明所以,看着她拆掉包装。
“这乌压压的人堆看着害怕,你也带着。”杨桉给谢树挂上耳朵,捏了鼻尖上的口罩让它更贴合,往下颌拉平有褶皱的地方,满意地看了看,“不错。”
谢树勾了勾唇角,摸摸杨桉的头,毛茸茸的,“我身体好,没事。”头凑过去就想亲近她。
杨桉一躲,脑袋往后退,食指戳着谢树的鼻尖,“昨晚说什么呢?”
谢树拿下她的食指完全覆盖,无奈微笑,“好好好,约法三章。”
简章如下:一,不在外面动手动脚;二,不在生气的时候,或者其他突发状况大手大脚;三,一切解释权终归杨桉。
秉承着谢树的理性,杨桉在被谢树亲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按下暂停,逼迫他签下霸王条约。谢树看她就差签字画押要公证的较真样,虽然无奈,碍于她还在生病,笑着宠溺地答应她,抱紧她好好睡觉。
等到最后半袋的针水,柯渊年打来电话,谢树看了一眼,安抚地拍拍杨桉,“我接个电话!”走到窗边接起。
杨桉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屯了很久的热血日漫,头都没抬地答应他,“嗯~”
接完电话回来,谢树敲了敲屏幕,“要不要去见一见左曦?”
杨桉怔忪,看着屏幕里的打斗和自己的脸混在一起,好像自己的内心也在混战,而谢树的眼神目光如炬。
适合吗?就不怕自己会知道些什么吗?他愿意对自己透露了?
“不去了,你有事就过去吧。”杨桉抬头笑开,单手反握回去,贴心地回答。
谢树看了时间,又看了一眼起码还有半个小时才能输完,“结束了,打电话给我。”
他上去一趟应该来得及。
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转角,杨桉拿出那份报告——听阀检测,虽然技术升级了,但是看着表格样式,几乎还是十年前的检测方法。
事实证明,那些打不死你的,可能会一直打你。
昨晚聂医生笃定她没什么大事,而且仔细问了杨桉头晕的症状,加上三个月无休止的工作,她的左耳可能出问题了。
趁着谢树离开的时间,杨桉开快了流速。
虽然极其不想深究,杨桉为什么下意识地想避开谢树,是不想让他担心,还是单纯不想说,或者她觉得就是无所谓的小事……
她自己也理不出清晰的理由。
州医院相比于十年前的规模更大,门诊大厅新建了一座四层高建筑,打通内部的所有连廊,导向所有出入口,两栋纯白色建筑合二为一,当年的那棵滇朴并没有被砍,而是长在了透光的天井里。
任何角度都一览无余这棵树的旺盛长势,从高阔的树叶里翻涌出氧气,生机弥漫着每一层的连廊,寡淡喧嚣的医院貌似也生长出坚不可摧的绿色,一直攀援升至顶层,杨桉站在树下,抬手接住静谧阳光,梦回成年那天的楼梯间的弱光。
当年的问题,没有在刘女士哪里得到回答,搁置了十年,她回答了自己:
“你不会好。”
仰头找寻聂尘炀,在二楼的围栏边上看见了人,杨桉上楼。
把报告转交到聂尘炀手上,便走到玻璃围栏往下看着,刚刚她站着的滇朴树下,小朋友扣着地面的米色碎石,旁边的父母和老人对着树下的碎光,抬高造影讨论着,偶尔摇头看看小孩子。
很神奇的感受,仅仅高出一楼的楼距,但是看到了亮堂光下的小朋友,经历和感悟给杨桉营造了一个上帝视角,像是能预见这小孩接下来的命运一样,一眼就推衍出故事走向。
回头聂医生也坐在木色的弧形座椅上,带着眼镜聚精会神研究杨桉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