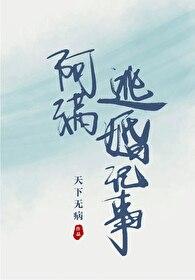02小说网>潇声生宵 > 争端(第2页)
争端(第2页)
她一看宋潇声说得满脸红润,显而易见是被气到了,一双狐狸眼带着冷光剜向了对侧。
抢在男人前面开口:“有些人眼睛不好使也就算了,嘴也跟着臭,别哪天祸从口出了自己还担当不起。”
男人握着卷轴的手一紧,他此时已经知道自己不占理,可仍是放不下所谓的面子。
他一直教导自己的学生,男女生来不同,男性顶天立地而女人则在家里打理家务。
他从小便这么认为,父亲这样教导他,他便这样教导下一代。
可今天,他却被自己一直忽视的女人折了面子。
他压下声音,沉声道:“你又来掺和什么?”
“我掺和?你方才看我在这弹琴估计也以为我是个便宜主儿吧?方才你的眼睛是黏在琴上还是黏在我的脸上你自己也清楚。”白玉生尖着嗓子道,“我看是你一直问我的事情,没听到想听的答案恼羞成怒了罢!”
男人被白玉生呛的一噎,觉得自己的肺下一刻就要炸了,一只胳膊指着白玉生和宋潇声不住颤抖,半晌后他脸上抽搐两下,极度不快地从嘴里啐出一句话:“像你们这样的女子,定落不到一个好夫家!”
话音一落,像是给自己找些气势似的,一甩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白玉生听笑了,对着远去的男人骂了一声,随后恶狠狠道:“哪个男儿像你这般天天拿女人嫁不出去说事儿?我看你读的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
原本还在围观的人在男人离开后走了一大半,白玉生见宋潇声脸上未消的血气干愣地站着,嘴里还带着点对男人的还没消散的怒气道:“站着干甚?你着生意还做不做了?”
宋潇声看了一眼桌子上被弄乱的纸牌,压下眼睛道:“做。”
白玉生愤愤地瞧了一眼远处:“晦气玩意儿!”
骂完之后就又推着轮椅去屋子后面做饭了。
宋潇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过这次她没拉帘子,觉得没必要搞这些神秘的玩意儿了。
宋潇声努力平复着自己快而深的呼吸,一双手在桌子上紧紧攥着,她眼睛一闭上便是刚刚那男人傲慢自负的模样就生气一股无名火,要是现在有个血压计来给自己测上一测她的收缩压肯定140+。
脑瘫。
宋潇声没忍住,在心里骂出来了。
她干直播干了一年多,还没遇到过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傻b。她又骂一句。
“这位姑娘?”
宋潇声睁开眼,对面坐了一个青色衣服的女人。
看着不过三十出头的样子,一身打扮也得体干净。
只是肤色黢黑,手臂上有着长短不一的红色划痕,像被野草划伤一般,而她的掌心还带着又糙又干的皲裂,一副常年干活儿的朴素模样。
是刚刚那个为自己说话的女人。
宋潇声心无声地软了,温和道:“您好,想测些什么?”
妇人看着宋潇声这么问,一时紧张了,她不懂这些牌的意思,也不懂这些规则,一双手此时有些局促不安,在身前无规律的晃着。
宋潇声见她的眼睛盯着自己的牌看,顿时懂了。
用手将桌子上的牌悉数扯下,搁置到一旁的木桩上。
妇人一看宋潇声把桌子上收拾的干干净净,心里忽然慌了,以为是自己浪费了时间,这生意不愿意给自己做了。
“我是不是耽误你了?”她不安的问道。
宋潇声摇摇头,随口道:“没事,您随便问。”
妇人还是有些不放心,又重复一遍:“随便问么?”
宋潇声点点头:“这些牌只起辅助作用,没什么影响。”
妇人眼睛眨巴两下,心想连道具都不用了,真的准么?
不过她方才也看见宋潇声是如何反驳那男人,心想这姑娘肯定不会忽悠自己,哪怕不准,也能求个心安吧。
索性将心里一直担忧的问题问了出来,她的声音沙哑的像黄土那样干涩,独有戈壁上刮起的风一样的寂寥。可是她问出来的问题却又带着些让人眼睛湿润的情绪。
妇人有意放低的声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真诚:“明年秋天,我的麦子会丰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