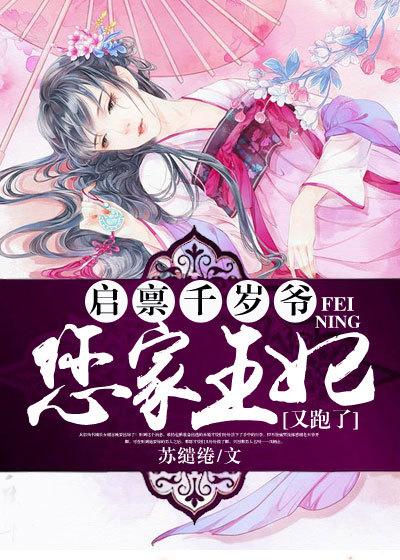02小说网>权宦对朕图谋不轨 > 第 14 章(第1页)
第 14 章(第1页)
那络腮胡并未停手,操着木棍就向二人打来,邵钰极力压着怒火,千钧一发之时将云灼护在身前,后背生生挨了几棍子。
他头上的束发银冠被撞得歪斜,墨发如瀑般散了大半,有几缕贴在汗湿的额前。长袍前襟沾了污渍,袖口的金线绣纹被勾出几道破口,瞧着有几分狼狈。
邵钰提了一口气,回身将人踹了出去,那人眼见落了下风,爬起身就要跑,云灼忙道,“抓住他!”
周围的锦衣卫应声上来,将还没跑远的人死死压在地上。
云灼上前抽出锦衣卫腰间的佩刀,泛着寒光的利刃抵着那人喉间,“谁派你来的?”
此人身强体壮,半点儿病气不见,她可以确定,他绝不是染了时疫的流民。
那人一双眼睛射寒星,冷哼一声道,“我只是个流民罢了,你要杀人灭口不成?有种你就来,我绝不会向你们这些丧尽天良之人屈服。”
云灼也不反驳,冷眼看着他,手中的佩刀又进了几分,那人脖颈上立刻出现连珠串似的血珠,“你最好想好了再说,话不要说的那么绝对。”
“要杀要剐随你们,你们这些衣冠禽兽,活该被天下人所唾弃。”
见他态度强硬,云灼也不恼,“你在这里负隅顽抗,就没想过,你的同伙也会如你这般冥顽不灵么?”
那络腮胡闻言愣了一下,身躯一震,抬头看了一眼云灼,又垂了下去。
云灼眼见这人已漏出破绽,乘胜追击,“你以为我如何肯定你的身份?若不是有人揭发,今日还真把你当流民错放了。”
这话一出,络腮胡的脸色瞬间煞白,原本紧绷的肩膀垮了下去,声音却依旧坚定,“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云灼语气平静,“听不懂?看来你不如他识时务,他安享荣华富贵,那你便替他去死吧。实话告诉你,只要他点头指认,你便是今日害死无辜百姓的罪人,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确定还要为你这可笑的江湖义气作无谓的挣扎么?”
说罢,邵钰稳步停在云灼身边,身后跟着的秦松庭上前在她耳边低语,目光却有意无意间落在络腮胡身上,“公子,在下已经验明,我们起的大锅里的药和那些死者所服药中皆被掺了砒霜,数量不多足以致命。”
云灼她寒声道,“他已全部招认,砒霜是你弄来的,聚众闹事是你起的头,把毒下进药里也是你的主意。”
“不必再查了,来人!把这贼子押到城楼上去斩首示众,尸身悬挂七日,让全城百姓好好看看他的嘴脸!”
“你做下此事便应当知道下场,罪名不小,足以轰动全城,治你一个谋反之罪你可有异议啊?夷三族的刑罚你一个人担着就是。”
这话像一道惊雷劈在络腮胡头上,听闻此残酷的刑罚,顿时慌了神,猛地挣扎着嘶吼,浑浊的眼泪夺眶而出,“不是!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是老三!还有老五!是他们跟我一起找的砒霜,下药的时候他们也在!”
他脸色涨得通红,为了脱罪,声音都破了调,“他们说这法子能让太子身败名裂,我才肯干的!他们怎么能把黑锅全扣在我头上?你们不能只抓我,要抓就把他们也抓来!”
络腮胡越说越激动,之前拼死抵抗的硬气,只剩重刑威逼下的恐惧与急于攀咬的狼狈。
“你们与太子殿下素未谋面无冤无仇,为何想让他身败名裂?”
络腮胡想了想,眼神有些飘忽,“皇家之人刚刚在上,哪里管我们底层老百姓的死活,换一个人做太子做皇帝都是一样的昏庸无道!”
云灼眯了眯眼,“你若把你幕后之人说出来,我便能留你一命,保你此生太平。”
让几个小喽啰认罪伏法没什么用,她要的是揪出那幕后之人。
他咬了咬牙,没有半分犹豫,跪伏在地上连连磕头,“此事与旁人无干,都是我们一时糊涂。”
眼见问不出什么,云灼将佩刀收入剑鞘,语气冰冷不带一丝温度,“押上城楼。”
那络腮胡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惊恐,被两个厂卫架着离开了。邵钰上前一步,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轻声道,“他说的那两人我先前便注意到了,今日之事是我大意失职,没有早点控制他们。”
“现在已将他们捉拿,听候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