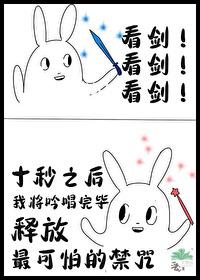02小说网>权宦对朕图谋不轨 > 第 14 章(第2页)
第 14 章(第2页)
云灼只觉得额角突突跳,十分烦躁,“你是怎么办事的,你就跪在这里静心思过,没有我的允许不许擅自起来。”
话一出口她便后悔了,好笑自己不自量力,邵钰权势滔天,怎么可能会乖乖听她的话,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她张了张口想要说什么抬眼瞥见邵钰不动声色的面庞,此刻他眼里翻涌着她看不明白的情绪。
“噗通”
他轻轻撩袍,一言不发地跪在她面前,身姿依旧挺拔,脊背没有弯曲半分。
“殿下息怒,奴婢领罚。”
他很倔,云灼看出了他眼里的桀骜和不甘。
气氛十分尴尬,她飞快移开在他身上的视线,带着厂卫往城楼处走去,“罢了,索性已经抓到他们了,也算你将功补过,起来吧,下不为例。”
邵钰垂着头闷闷答谢,拍打衣裳的声音传入耳中,紧接着便是缓慢沉重的脚步声,云灼忍住没有回头。
城楼的风带着凉意,刮得云灼鬓边碎发乱飞。厂卫引着她踏上石阶,厚重的城门在身后吱呀作响,将邵钰那缓慢的脚步声彻底隔断。
她指尖无意识攥紧了袖角,方才邵钰趴在地上时,她瞥见他膝盖处的衣料沾染了污秽,与他一向矜贵和高高在上的姿态大相径庭,她有些心虚,当着众人的面责罚了他,叫他下不来他,不知他是否会记下这笔账。
“公子,人已押至箭楼听候发落。”厂卫停下脚步,躬身禀报。
云灼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莫名的滞涩,抬步踏入箭楼。
今日事发突然,她不便出面,只得以太子随侍的身份处置几人。
她看了一眼押着人的厂卫,那厂卫会意,将人按在垛口处,云灼见城楼下已经围了好些看热闹的流民,心知时机已到。
她侧过身,目光扫过络腮胡煞白的脸,声音比楼外的风更冷,“这里有这么多百姓看着,你便当着他们的面,用心悔过你的罪行。”
络腮胡喉咙里滚出浑浊的呜咽,被厂卫按在垛口边时,他往下瞥了眼黑压压的人头,突然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嘶吼,“我错了!那砒霜是老三寻的,下药时老五也在,是我们鬼迷心窍攀污了太子殿下。”他越说越急,唾沫星子溅在青砖上,“是、是有个穿青衫的人找我们!说太子庸懦无为…”
这话一出,城楼下的议论声陡然拔高,云灼眼底寒光一闪,果然有幕后之人。
她没立刻追问,只抬手示意厂卫按住躁动的络腮胡,声音透过风传到楼下,“诸位百姓听着,此人勾结党羽,意图用毒谋害诸位以嫁祸给太子殿下,今日斩他示众,便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残杀无辜,扰乱朝纲者,纵有同党,纵有靠山,殿下也绝不会轻饶!”
“公子。”身后忽然传来轻唤,云灼回头,竟见邵钰站在箭楼门口,玄色衣袍上的尘土已拍去大半,只是膝盖处仍隐约可见浅痕。
“老三和老五既已抓获,”邵钰声音压得极低,“奴婢已让人严加审讯,那穿青衫的人,或许与皇后有关。”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骚动。络腮胡盯了半晌流民,突然疯了般挣开厂卫,朝着垛口外大喊,“我是冤枉的!太子叫人严刑逼供于我,让我当替死鬼,在这哄骗天下人替他遮掩罪行,我是冤枉的啊!”
“太子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救你们,巴不得你们全都被毒死!他们没有办法治愈时疫,如此好为朝堂省事。”
“住口!”云灼厉声喝止,可这话已像石子投进沸水,城楼下的议论声瞬间炸开。她飞快看向邵钰,见他眼底也凝了霜,两人无需多言,厂卫已再度将络腮胡按死在青砖上。
络腮胡的嘶吼像淬了毒的石子,砸在城楼下的流民堆里,瞬间炸开了锅。有人往前挤着嚷嚷“真的假的”,更有几个裹着破棉袄的汉子,竟捡起路边的碎石子往箭楼上扔,石子撞在青砖上“当啷”作响,混着“太子草菅人命”的骂声,风里满是躁动的戾气。
云灼的指节在袖中攥得泛白,她强压着心头的惊怒,踏前一步,声音穿透嘈杂的鼓噪,字字清亮,“你说殿下严刑逼供?方才在城楼下,是谁先招认砒霜是你弄来、闹事是你牵头?现在想反口诬陷,当这满城百姓都是瞎的聋的不成?”
话音刚落,邵钰已上前半步,左手举起一方染了墨痕的纸笺,右手按在腰间佩刀上,沉声道,“这是老三、老五方才画的供词,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是穿青衫的人让他们栽赃太子殿下。”
云灼一时间难以从这连珠炮似的变故中缓过神来,哪里来的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