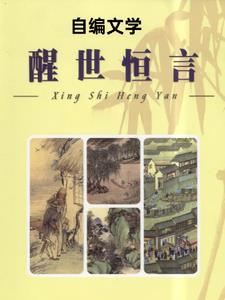02小说网>给新皇当狗腿后他决定断袖(双重生) > 7080(第15页)
7080(第15页)
李定睿见周思仪仍旧埋头俯首不起,他沉声道,“你如今不过二十来岁,尚未知晓生活的艰辛,有一个好的岳丈家也对你的仕途有所裨益。你还在孝期当中,我们偏怜幺女也不愿意她早早嫁人,你还有的是时间考虑与我女儿之间婚事。闻之,好生想想你的前途才是!”
从私塾中走出后,周思仪擦了擦额角的冷汗,她的后背已然全部沁湿了。
蒋王允了她这些日子仍旧在私塾中教书,她告了绕就回道观备课去了。
却不想刚一踏入道观,就被这小道姑缠了上来,她的道袍一向比观中其他人精致上好些,宽松飘逸的袍子却特地将腰线掐了起来,显得人身姿窈窕,打籽绣的梅花纹样让花蕊越发灵动,若是春日里,指不定有几只蝴蝶落在上面。
周思仪思衬了良久,她如今的法子唯有一个拖字诀,这守孝之期是长是短全凭她一张嘴,郡主也不可能一直等她,可惜云浓不在扬州,不能帮她遮掩一二。
周思仪应付这些长安贵女的热烈痴缠独有一套办法,知道她们这样被偏疼长大的女儿至多不过半刻钟热情,一开始见她长相俊俏心动,等过些日子发现她性格迂腐,也就日渐淡了。
“闻之,你下午打算做什么?”
周思仪垂下头道,“练字看书,准备科考。”
往往每当她说出这些,李羡羽就自讨没趣地走了。
谁知李娴清却显然比李羡羽难缠上十分,她兴奋地一拍手道,“正好,我新得了几本杂记,每过午后,琼花台上日头温而不烈,我们一同在那里看最好不过了。”
周思仪抚了抚自己的胸口,她安慰着自己道,李羡羽也是这样,说要陪她一起看书,但每次只看了一两页就抱着书卷在贵妃榻上睡着了。
不足为惧、不足为惧。
琼花台寂静冷清,石阶上未消的晨露洒着细碎的晶莹。琼花树尚未到花期,只零星地落下几片碎叶。
“闻之,你可曾见过琼花吗?”
周思仪摇了摇头,“这是我第一次下扬州。”
“史书中载,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就是为了到扬州一赏琼花仙葩,可隋炀帝花没看成却亡了国,宋代仁宗徽宗孝宗三朝皇帝都曾欲把琼花移植到皇宫当中,却终至花萎树死,有人说琼花是亡国之花、不详之花,闻之,你也这么认为吗?”
“炀帝好大喜功,宋代积贫积弱,都是自上而下今年累月促成的结果,岂能是一花之过耶?”
李娴清声音悠远,娓娓道来,“闻之,你知道吗?从长安城传来了一个八卦,说故去的周相公,他的小儿子周思仪纱帽罩婵娟,明明是女儿身却扮作男儿郎,入朝为官数年,被圣人发现了,圣人非但不计较她女扮男装的过错,还要娶她,迎她为皇后。”
“可是这女人却不愿意,借着一场大火逃了,逃到天南地北,皇帝抓不着的地方去了,”李娴清在琼花树下驻足而立,一片落叶掉落在他的掌心,“我听了这个故事,只觉得她就像这琼花一样。”——
作者有话说:(1)旗亭画壁:故事出自薛用弱的《集异记》
放一下我隔壁的预收文案,主打一个阴湿太子巧取豪夺豪夺漂亮妹宝。
李簪月以头撞柱,记忆全无。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仅有了丈夫,竟还有了一位……权势滔天的情人。
新朝太子元昼俊美无俦,却狠戾薄情。
云收雨住之时,她总是颤声求饶,欲斩断这桩孽缘,重回夫君身侧。
元昼便用冷得不能再冷的眼神瞅着她,字字诛心,“当初,是你蓄谋勾引我的。”
——
脑子撞坏后,李簪月觉得她的夫君谢修齐是天下第一好郎君。
他会为她洗手作羹汤,风雨无阻地喂她喝药,会在她头疼难忍的时候哼着童谣哄她入睡。
可她却舍了这样好的夫君,与太子日日苟合,做尽毫无廉耻之事。
“月娘,这样的力度你可还满意?”
每每耳鬓厮磨,李簪月含泪不语,实在不堪受辱。
她备受这段三人婚姻的折磨,一度自暴自弃再不饮药,却发现停药之后,自己的脑子竟越来越清明。
直到那日,她赫然发现:
哪有什么完美的郎君,日夜相对的谢修齐,竟是太子元昼假扮的!
恩爱过往,不过作戏,只为了看她沉沦堕落,看她一女侍二夫的丑态。
——
元昼视角:
从前,他的夫人李簪月走马拂花枝,买笑倾黄金,是天地安危两不知的长乐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