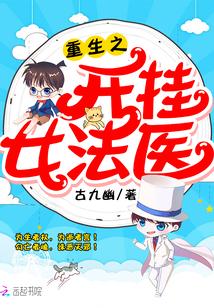02小说网>本王的科技树长歪了 > 量产困境(第1页)
量产困境(第1页)
公开测试的胜利,如同给赵楷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为他推行的“标准化”和“新工艺”赢得了宝贵的喘息空间和官方背书。枢密院正式下文,批准将仿制神臂弓(曹玮将其更名为“靖虏弩”,以示区别并避嫌)列入小批量试产,由将作监负责,赵楷具体督办。
然而,从“实验室样品”到“规模化生产”,这其间的鸿沟,远比赵楷想象的要深、要宽。
第一个跳出来的拦路虎,就是他那“歪打正着”搞出来的“赵氏土法无机胶合剂”。
测试时,他可以用心挑选最新鲜的猪血、最细腻的石灰、亲自盯着火候搅拌,做出性能不错的胶。但一旦要量产,问题就全来了。
“赵先生!今日送来的猪血……腥气太重,还掺了水!根本没法用!”
“石灰粉批次不一样,细度差好多,和上次的混在一起,结块了!”
“这蛋清……怎么这么稀?是不是掺了鸭蛋?”
“天气突然返潮,调好的胶半天不干,全废了!”
工坊里抱怨声此起彼伏。负责调配胶剂的工匠愁眉苦脸,材料的不稳定和工艺的模糊性,导致胶合剂的质量波动极大,直接影响了复合弓臂的层压质量。废品率居高不下,生产效率极其低下。
赵楷焦头烂额。他意识到,手工小批量制备和工业化生产完全是两码事。没有原材料标准,没有工艺参数,没有质量控制,所谓的“量产”就是一句空话。
他不得不再次化身“土法科研员”,扑在胶合剂的生产线上。
“定标准!必须定标准!”他对着孙主事吼道,“猪血必须新鲜,无掺杂,取血后半个时辰内必须送到!石灰必须过细筛,统一目数!蛋清……蛋清……”他卡壳了,蛋清这玩意怎么定量?“蛋清……就用固定大小的鸡蛋!十个鸡蛋取清,兑多少水……呃,兑多少猪血和石灰,必须固定!”
他强行制定了一系列简单粗暴的“原材料验收标准”和“调配比例”,虽然依旧粗糙,但至少有了一个可执行的框架。
接着是工艺。加热温度怎么控制?没有温度计,他让人在锅底撒一层细沙,观察沙子开始轻微跳动时的火候(约60-70度),定为“文火”。搅拌时间?用沙漏!虽然不准,但比凭感觉强。固化环境?搭建简易的“烘干房”,地面铺石灰吸潮,尽量保持干燥。
一套组合拳下来,胶合剂的质量稳定性总算有了一点点提升,但依旧远谈不上理想。量产之路,步履维艰。
与此同时,弩机金属部件的标准化生产也遇到了麻烦。
尽管赵楷提供了详细的图纸和简易量规,但将作监的金工匠人们习惯了“差不多就行”的自由发挥,对严格按照图纸和公差生产极其不适应,效率反而不如从前。
“赵先生,您这要求太严了!这轴多做一丝一毫,又要返工!耽误工夫啊!”
“这孔稍微偏一点,装的时候敲两下就进去了,何必非得卡得那么死?”
“量规?用着麻烦!俺闭眼一摸就知道合不合适!”
老师傅们的抱怨声不绝于耳。张匠头更是阴阳怪气:“有些人啊,就知道纸上谈兵,根本不懂匠作之道!照这么弄,猴年马月才能交差?”
赵楷气得肝疼,却又无可奈何。他知道,改变固有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模式,需要时间,更需要强有力的管理和激励机制。
他不得不再次求助曹玮。曹玮对此倒是十分支持,直接下令:靖虏弩生产专设工坊,工匠择优遴选,按新法作业,计件核功,优赏劣罚!抵触怠工者,严惩不贷!
有了上峰的强硬态度和实实在在的利益驱动(干得好能多拿钱),工匠们的抵触情绪才被强行压了下去,开始不情不愿地学习使用量规,严格按照图纸加工。
生产效率在经历初期的阵痛和下滑后,开始缓慢回升,加工出零件的互换性果然提高了,后期组装调试的工作量大幅减少。
张匠头等人虽然表面服从,但私下里的怨气更重,看赵楷的眼神愈发不善。
就在赵楷忙于应付量产的各种琐碎难题时,王貺的弹劾果然如约而至。虽然测试失败了,但他转而攻击赵楷“玩法弄权,苛待工匠,徒耗国帑,量产无期”,奏本里充斥着“怨声载道”、“进度迟缓”、“质量参差”等字眼。
这些攻击并非空穴来风,确实戳中了赵楷目前的痛处。量产不顺是事实,工匠有怨气也是事实。
曹玮再次顶住了压力,但私下召见赵楷时,语气也严肃了许多:“王御史所言,虽多夸大,然亦非全然虚妄。量产之困,你当心中有数。若迟迟不见成效,恐难堵悠悠众口。”
赵楷冷汗直流,只能保证尽快解决。
压力之下,他做出了一个更加“离经叛道”的决定——建立简易的质量检验流程。
他在生产线的几个关键节点设置了“检验岗”,由他信任的学徒工手持简易量规(过不过规、塞规、平尺等),对半成品进行抽查。不合格的,当场退回返工!屡教不改的,记录在案,扣罚工钱!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