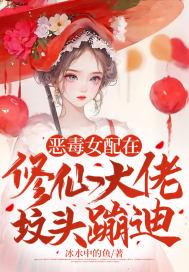02小说网>本王的科技树长歪了 > 陛下视察(第3页)
陛下视察(第3页)
王貺在一旁听得心急,忍不住插嘴道:“陛下!新法虽好,然其用料讲究,造价不菲,恐非寻常农户所能承受。且骤然更改旧制,恐引民间不适……”
赵楷立刻反驳:“王御史所言差矣!标准化非为追求奢华,乃为保障基础品质。统一制式后,大批量制作,成本反可降低。且旧车易坏难修,新车耐用省心,长远看,农户负担实则减轻!”
工部尚书也想挑刺,指着纺车道:“此车传动似与军器相关,挪用军技于民,是否妥当?且如此改进,于织锦缎等精织之物,可有裨益?”
赵楷不卑不亢答道:“回尚书大人,技术本无军民之分,利于民生便是正道。至于精织,此车主打提升粗纱、棉纱效率,若要织锦,需另研精纺机,然其‘标准化’思路,亦可借鉴。”
他回答得滴水不漏,始终紧扣“普惠”、“实用”和“方法论”的主题。
赵祯听着双方辩论,并未表态,但看向赵楷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深思。
观摩完毕,赵祯并未立刻离开,而是在曹玮、吕夷简的陪同下,步入一间静室,单独召见了赵楷。
室内只剩下皇帝、宰相、枢密使和赵楷四人。气氛顿时变得更加凝重。
赵楷跪在地上,心知真正的考校才刚刚开始。
“赵楷,”赵祯缓缓开口,“你之所为,朕已亲眼所见。新法确有实效,尤以‘标准化’、‘规程化’之思,颇具巧思。然,朝中于你,争议颇大。朕今日问你,你此法,究竟源出何处?所图为何?”
终于问到核心了!赵楷深吸一口气,将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和盘托出,只是更加诚恳:
“回陛下,小子之法,并非凭空而来。一者,源于修复古器之实践(指南车),深感古人工匠之精妙,然其法失传,令人扼腕;二者,源于军械制造之困局,零件互异,换修艰难,废料耗工;三者……三者亦受先贤著述之启发,《考工记》有云‘审曲面势,以饬五材’,《墨经》亦言‘法仪’之重。小子只是……只是将散见之智慧,加以梳理,强名之曰‘标准’,力求将良工之巧思,化为可传之法度,使精良之器,可复可广,而非囿于师徒口耳之间。小子所图,无非‘国强民富’四字。军械精良,则将士无忧;百工增效,则民生可期。此心此志,天地可鉴!”
他半真半假,将现代理念包装在古代经典之中,听起来既接地气,又有理论高度。
赵祯沉吟片刻,又问:“然则,革新必触旧例,易引纷争。你当如何自处?”
赵楷恭敬道:“小子深知此理。故而行事务求谨慎,先易后难,先军后民,以实效取信于人。若有纷争,愿以事实数据说话,是非曲直,自有公论。若小子之法确有疏漏,亦当及时修正,断不敢固步自封。”
态度谦逊,逻辑清晰。
赵祯听完,良久不语,目光扫过吕夷简和曹玮。
吕夷简缓缓开口道:“赵楷虽年轻,然其思其行,确有利国利民之实。然其法颇新,争议难免,当引导其扬长避短,稳妥推行,方为善策。”老狐狸依旧是和稀泥,但基调是肯定的。
曹玮则直接道:“陛下,军械改制,成效卓著,此乃实事。赵楷虽有孟浪之处,然其才可用,其心可嘉。当护其锐气,以观后效。”
赵祯终于点了点头,对赵楷道:“朕姑且信你之志。然需谨记,匠作之术,终为末技。强国之本,在于仁政,在于民生。你之新法,当服务于国策大局,而非为技而技。日后行事,需更加沉稳,多思大局,少惹纷争。可能做到?”
“小子谨记陛下教诲!定当恪尽职守,不负圣恩!”赵楷连忙叩首,心中一块巨石终于落地。皇帝这一关,总算有惊无险地过了!
“嗯。”赵祯摆摆手,“下去吧。”
赵楷躬身退出静室,只觉得浑身虚脱,仿佛打了一场恶仗。
皇帝摆驾回宫后,王貺等人虽然心有不甘,但见陛下态度明确,也只能暂时偃旗息鼓。
赵楷回到工坊,立刻被众人围住。
“郎君先生,怎么样?”众人急切地问。
赵楷长长舒了一口气,露出一个疲惫的笑容:“暂时……过关了。”
工坊内顿时爆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声。
然而,赵楷还没来得及高兴,曹玮的亲随就来找他,面无表情地传达了一句口信:“曹大人说:军弦之事,下不为例。你好自为之。”
赵楷刚刚落回肚子里的心,又提了起来。曹玮果然知道了!这是在保他的同时,也在严厉警告他!
挪用军资,这是大忌!这次侥幸过关,下次绝不会这么幸运!
科技树又一次在悬崖边上惊险地稳住了根基,但赵楷深知,自己行走的钢丝之下,依旧是万丈深渊。未来的路,必须更加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