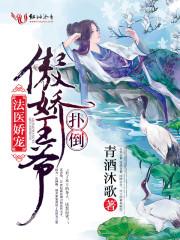02小说网>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33章 旧事(第1页)
第33章 旧事(第1页)
江临舟那天晚上睡得很早。
他没有翻来覆去,也没有特意去回想唐屿的那句话。
灯熄之后,他只是平静地闭上眼,像往常无数个练琴结束后的夜晚那样,让疲惫顺着脊背沉下去。
但梦却在夜半不请自来。
他梦见了那个夏天,第一次见傅义的那天。
那时他才九岁,被母亲领着穿过一条静得出奇的小巷。旧小区的门牌褪了色,铁门半掩着,一楼一户的窗口挂着泛白的花布帘。
屋里很安静,像图书馆,也像寺庙。
傅义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袖口整整齐齐,坐在立式钢琴旁。他的眼睛很亮,但神情不温不火,像在等一件东西沉到底。
“先弹一个音给我听听。”他只说了这一句,便不再出声。
江临舟那时候不懂“好不好听”,也听不太出音准,只记得指尖落下去的那一下,傅义的眼皮微微抬了抬。
“坐得还算稳。”那是他对这个孩子的第一句话。
梦境悄然跳转,浮光掠影般闪过无数个练琴的午后和黄昏。
琴房的木地板踩上去有些松动,窗框被阳光烤得微微褪色,角落的风扇慢吞吞地转着。
“从这里开始,别再提气。”
傅义低声说,语气平稳得像是在念一段旧经文,
“把句子送出去,不要推。”
琴键在梦中仿佛没有了阻力,指尖落下去,是一片水面。
他依稀记得那是第一次练肖邦的夜曲。
那年他十一岁,盛夏,屋里没有空调,只靠电风扇摇头缓解热气。
傅义坐在他左边,闭着眼,手指在空气中比划旋律的走向。
“弹肖邦,要像在歌唱。”
老人语气缓慢,“不是每个音都要推出来,也不是每个音都要藏起来。重音要唱得出气,弱音要留得住气。”
后来,他十四岁那年,傅义坐在老式收音机前,播放一段德彪西的《映像集》改编录音。
“听,”他说,“要分得清谁在拉节奏,谁在挂线条。”
“你不能靠上台时‘对拍子’去合乐队,你要从练习第一天就听进去。”
梦境中的少年坐得笔直,嘴唇紧抿,眼睛却一瞬不瞬地盯着傅义的手。
然后是最后的冬天。
屋里很冷,风从窗缝灌进来,电风扇已经坏了。
傅义靠在旧藤椅里,身上盖着一层薄毛毯,面前的谱子摊开着,却没再翻动。
他已经不太说话了,偶尔咳嗽,眼神却依旧清亮。
那天下午他没有教琴,只叫江临舟坐在他旁边听了一段录音,是很早以前他自己的演出。
“你以后可能会赢,但别让人听完你的琴,记得的只有‘赢’。”
那是傅义对他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
他又梦见了那间病房。
冷白色的墙面,洗得过度的床单,消毒水味混着一丝冷铁气味,从门口一直延伸到窗边。
傅义躺在床上,身体像被压成了一块轻薄的影子。
脸瘦得几乎脱了形,眼皮下陷,颧骨突出,嘴唇干裂而微微张着,像是还停留在一句话的中段,却再也接不下去了。
他穿着病号服,手背上插着针管,手指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