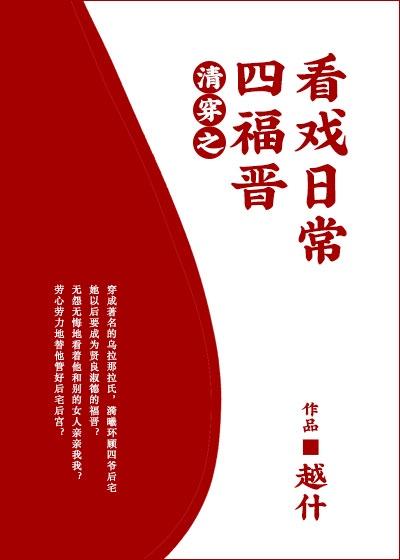02小说网>吾妻万人迷 > 凯旋(第2页)
凯旋(第2页)
……还不回来,是要和他们睡在一起吗。
他很少因旁人心绪难平,又去桌前提笔练字。
铜壶滴漏催晓,夜色越浓,他越提不上气,像染了风寒的病人,呼吸滞涩,胸腔被墨汁充胀得满满当当,竟无法静心。
每落成一横,便会走神;一竖,似她袅娜的身姿;一撇,好像她没骨头挨在他身上的模样。
你曾说,旁人吃完你做的东西时,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可我已咽尽你做的芝麻饼,你却迟迟不惠顾我的枕边。
明明说过心悦我。
床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詹景行阖眼装睡,身侧沉下一小块。
詹狸见他的手放在被子外边,抬起来,往被子里面腾腾位置,想塞进去,却倏然对上了他的双眼。
“很晚了,你还没睡吗?”
你也知道很晚。
詹景行卡住她的手,让她无法抽离。他摩挲她无名指处的紫翠,反复扭转那枚指环,试探着卡得更紧,仿佛这样便能将她牢牢锁住。
詹狸拍打他的手背:“别摸花了,这可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
他知道她一直很珍惜,不论是因为镶的金,还是紫翠,都算珍、爱他。
“吻我吧。”詹景行闭上眼睛,似乎有些疲惫,更多是惶恐。
詹狸犹豫半天,才撑住床沿,将柔软的双唇送入他唇间。他抬手掌住她的后颅,吮走她舌尖,以一副下位者的姿态,掠夺她的温度、香气与潮水。
詹狸不知道,她学不会换气,长睫总被泪氤氲,湿漉漉的很是可怜,像他把她欺负得狠了。唇瓣翕张,却是他在求救,他在低泣。
“你会退他们的聘礼,对吗?”
“嗯……”
单一个嗯字不能抚慰他的不安,于是吻愈往下,叫她急急扯住了他的乌发。
“那里不能亲!”
“可是我想。”
“想也不行!”
“不给你的相公亲,那给谁?外边的情郎么?还是两三个,你招架得住吗。”
詹狸因为这话羞红了脸,哪有自家相公这么说娘子的!
头发被扯痛,取而代之,他在她膻中留下一个红印。詹狸试着去推詹景行,但这人纹丝不动,只是埋在柔软前,静静的,似乎在想事情。
“狸狸。”
胸膛发出一阵闷闷的回响,他却不想永远空荡。
“我爱你。”
詹狸没有回应。
#
洒扫的丫鬟捧着铜盆,后厨的伙计提着鲜鱼,詹府到处张灯结彩,下人皆步履匆忙。见春荷忙不过来,詹狸自个儿爬上了木梯,将写有“状元及第”和“乔迁之喜”的红灯笼挂上檐角。
詹狸左看右看,还是觉得歪了些。
她没踩稳木梯,整个人往旁侧一晃,吓得紧紧抓住身下的木条。本来都快翻落了,不知是谁搭了把手,把木梯扶正。
“多、多谢,差点要在大喜的日子交代了。”她拍了拍胸膛,才垂首看是谁帮了自己。
曹昀面色不虞,咬文嚼字:“大喜的日子?”
詹狸心下一跳,本就惊魂未定,眼下更是慌乱,偏偏他还抓住了她的脚腕,蹬也蹬不开。
要是被外人看到…探花在詹府面前抓着一女子的腿,成何体统啊!
“曹昀,放手!我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