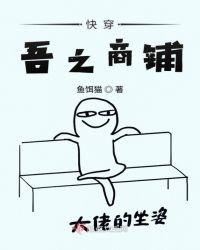02小说网>惊鸿宴 > Chapter 15(第5页)
Chapter 15(第5页)
“我今晚睡书房。有任何情况,立刻叫我。”
“好的,夫人。”
书房的门轻轻关上,隔绝了走廊的光线,也仿佛暂时隔绝了那扇紧闭的卧室门带来的沉重压力。徐敏没有开大灯,只拧亮了书桌上的一盏台灯。昏黄的光晕照亮一小片区域,更显得书房空旷冷清。
她没有洗漱,只是脱掉了高跟鞋和外搭的披肩,和衣倒在书房那张宽大的皮质沙发上。丝绒礼服在身下发出细微的摩擦声,提醒着她刚刚结束的喧嚣与此刻的孤寂形成的巨大落差。
身体的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但大脑却异常清醒。宴会上那些恭维、灯光、香槟气泡仿佛已成隔世,只剩下门外那片沉甸甸的寂静,以及寂静背后那个让她牵挂又无力靠近的人。
她以为自己可以暂时用虚荣和忙碌麻痹自己,却原来,那根线一直牢牢系在姜妤曦身上,轻轻一扯,便是撕心裂肺的疼。
而此刻,一墙之隔的主卧内。
厚重的窗帘遮住了夜色,房间里一片昏暗,只有床头一盏小夜灯散发出微弱朦胧的光。姜妤曦并没有像徐敏和管家猜测的那样,虚弱地躺在床上。她靠坐在床头,怀里抱着一个软枕,目光落在虚空中,脸上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只有一片沉静的漠然,以及眼底深处一丝极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倦意。
她的身体并无不适。下午从孤儿院回来,阳光和孩子们的笑脸带来的短暂暖意,在踏入这栋冰冷华丽的宅邸时便迅速消散。尤其是看到徐敏留下的那张“有晚宴”的简短纸条时,那种熟悉的空洞感再次弥漫开来。
又是宴会。又是那些衣香鬓影,觥筹交错,虚伪的寒暄和膨胀的虚荣。徐敏的世界永远充满了这些,而自己,似乎永远只是她庞大生活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可以暂时搁置的注脚,一个需要用金钱和愧疚来安置的旧日幻影。
白天在孤儿院,徐敏主动提及老巷子,确实像一根刺,扎进了她早已结痂的伤口,带来一阵尖锐的隐痛。但更让她感到冰冷的,是徐敏那试图透过往事建立联系的姿态,以及自己那句话说出后,对方眼中一闪而过的、真实的痛楚。
她恨徐敏吗?或许。但更深的,是一种无尽的疲惫和绝望。她们之间隔着的,早已不是爱恨情仇那样简单分明的东西,而是经年累月的伤害、无法弥补的愧疚和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堆积成的巨大冰山。徐敏的任何靠近,都像是在提醒她这座冰山的存在,以及冰山下埋葬的一切。
所以,当确认徐敏又去奔赴她的名利场时,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一个幼稚的,甚至有些可笑的念头。
她想看看,如果自己“病了”,如果自己需要,在那个浮华的世界和自己之间,徐敏会怎么选。
于是,她告诉管家自己身体不适,不想被打扰,锁上了门。她甚至暗示管家,可以告诉徐敏情况不太好。她想知道,徐敏是会立刻抛下她的宴会,她的虚荣,她的体面,回到这扇紧闭的门外,还是会像以往无数次那样,选择她那个光鲜亮丽的世界?
当管家在电话里向徐敏汇报时,她其实就站在门后,静静地听着。电话那头徐敏的声音透过门板隐隐传来,冷静,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医生、心理医生……然后,是那句“我这边很快结束”。
那一刻,姜妤曦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感觉。并没有失望或愤怒,反而是平静。
看,这就是答案。在徐敏的价值排序里,自己终究敌不过一场重要宴会的体面。
她回到床上,听着楼下的动静。医疗团队来了,又走了。心理医生来了,也无功而返。管家在门外小心翼翼地劝慰。这一切,仿佛一场与她无关的闹剧。
直到徐敏回来。那急促的高跟鞋声,那带着担忧和急切的敲门声,那一声声放软的呼唤……姜妤曦只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连呼吸都放得轻缓均匀,仿佛真的沉睡。她听到徐敏声音里的疲惫,听到她最终放弃,走向书房的脚步声,听到书房门关上的轻响。
房间里重新陷入彻底的寂静。
姜妤曦缓缓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上昏暗的光影,许久,轻轻地、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这声叹息里,有对自己可笑行为的自嘲,更多的,是深不见底的疲惫和茫然。
骗她回来,又如何呢?回来了,站在门外,说着担心的话,然后呢?她们之间,又能改变什么?
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又一次验证了那令人绝望的现状。
她翻了个身,将脸埋进柔软的枕头里,隔绝了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也试图隔绝心底那片荒芜的冰凉。
夜,还很长。
书房里,徐敏在沙发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脑海中一会儿是宴会的流光溢彩,一会儿是姜妤曦阳光下短暂的笑颜,一会儿又是那扇紧闭的、沉默的房门。虚荣带来的短暂满足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冰冷的现实和噬心的担忧。
而一墙之隔,姜妤曦在寂静的黑暗中睁着眼,同样无法入睡。试探有了结果,却没有带来任何解脱,只让那无形的枷锁,似乎又沉重了几分。
这座华丽的牢笼里,两个被各自心魔和过往禁锢的灵魂,在同一个夜晚,不同的空间里,共同咀嚼着这份无声的、冰冷的煎熬,无人知晓。
长夜漫漫,似乎永无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