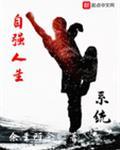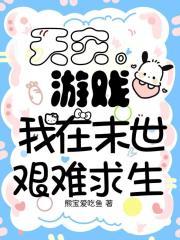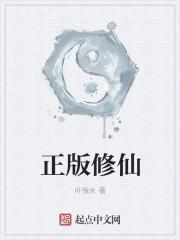02小说网>为变法,我视死如归 > 第238章 我快把高昌给整灭国了我咋不知道呢(第1页)
第238章 我快把高昌给整灭国了我咋不知道呢(第1页)
对于王小仙的提议,梁太后自然不可能拒绝,有意见。
给她钱花她凭什么还能有意见?
就算是限定了专款专用吧,可这西夏朝廷不可能不在款项上搞截留,搞贪腐的,修铁路和种树是给工资的,朝廷可以通过指。。。
风雪一夜未歇,统万城内外银装素裹。王小仙的灵柩停于文庙废墟前临时搭起的白棚之下,覆以素缎,四角悬铃,随风轻响如低语。百姓自四面八方涌来,不需官府号令,不待文书传召,扶老携幼,步行百里,只为看先生最后一眼。
苏辙立于棚前,双目红肿,手中握着那封尚未拆封的遗诏副本??那是李婉儿亲手交予他的,说:“他临终前只嘱咐一句:若朝廷问罪,便以此奏为证。”此刻他凝视着灵前烛火,心中翻涌的不是悲痛,而是恐惧:怕新政如春冰薄脆,一朝崩裂;怕十年心血,终成泡影。
阿勒坦披麻戴孝,率巡检司将士列队守灵。他们不再佩刀挂甲,而是人人胸前别着一方粗布抄写的《赋役对照表》,如同佩戴功勋章。王大虎则带着新编练的民兵营,在城外校场彻夜操演,枪矛齐举,口号震天:“守渠!护法!继志!!”声浪穿破寒雾,直抵城中。
第三日清晨,蔡京匆匆赶来,面色铁青。“出事了。”他在苏辙耳边低语,“昨夜驿马加急,京中御史台重启弹劾,三十余道奏章齐发,指‘王小仙专权跋扈,私设官衙,结党营私,形同割据’,更有甚者,称其与辽人密约,图谋自立。”他顿了顿,“韩维大人再度上疏求情,却被贬知邓州。”
苏辙冷笑:“他活着时,他们不敢动;他死了,反倒要鞭尸定罪?”
“更糟的是,”蔡京压低声音,“圣旨虽准五司试行,但枢密院已下令调走河朔驻军三万,改由中央禁军接管边防。同时,户部派来‘审计使’十人,即日启程,名为核查账目,实为夺权。”
苏辙闭目良久,忽而睁眼:“那就让他们查。阳光账册十年无虚,不怕对质。但有一条??绝不能让任何人玷污先生的遗志。”
当日下午,数百名学堂教习联袂而至,手持誊抄本《河朔新政实录》节录,请求将此书列入灵祭供品。一名老儒颤声道:“此书乃先生心血所凝,胜过金玉香火。若焚之,是焚民心;若存之,是续薪火。”众人齐跪,恳请入祭。
苏辙含泪应允。于是,在王小仙灵前,除香烛纸钱之外,又堆起一座由千余册手抄本书籍垒成的小山。夜幕降临时,百姓自发点燃蜡烛,围成巨大圆阵,少年学子轮流诵读《实录》篇章,声声入耳,句句如钟。
就在此时,一名十一二岁的牧童牵马而来,衣衫褴褛,脸冻得通红。他从怀中掏出一本用羊皮包裹的册子,递到苏辙面前:“先生……这是我在黄河渡口替人放羊时,跟着一位老师傅学的。他说,这是王大人留下的‘种子书’。”
苏辙翻开一看,竟是《五司一体纲要》的简写本,字迹稚嫩却工整,页边还画着孩童理解的图画:一个衙门分成五个屋子,每屋门口站着不同百姓推选的人。最后一页写着一行歪斜大字:“长大我要当民政司长,不让爹娘多缴一斗粮。”
苏辙双手颤抖,久久不能言语。
七日后,出殡之日。全境罢市,商旅停行,连西域驼队也解鞍卸货,披白致哀。灵柩由八十名民夫抬行,路线绕城一周,途经北岭渠、水泥厂、新学堂、市集广场。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百姓伏地叩首,妇孺哭声震野。
行至渠首石台,忽闻鼓乐声起。原来是工程司全体工匠列队而来,每人肩扛一块青石,上刻一字,拼成一行大碑文:“为民开渠者,永享春水。”
而在文庙重建工地,百余名少年正挥锤夯土。他们皆为“火种计划”首批遴选之人,最小者仅十岁。此时齐声高唱《咨议歌》:“官非主,法为尊;税有度,民可询!”歌声嘹亮,穿透风雪。
送葬队伍缓缓前行,直至城南山坡。此处早按王小仙生前遗愿辟为“平民墓园”,不分贵贱,凡为新政出力者皆可安葬。他的墓穴并不高大,唯有一块无字碑立于其前。
苏辙捧着那封奏章,站在墓前朗声宣读:“臣死之日,即是清白证明之时……”
话未说完,天空骤然放晴。乌云裂开一道金光,洒落在碑上,宛如天启。人群中爆发出低呼:“先生显灵了!”
就在这肃穆时刻,快马疾驰而来。一名驿卒滚鞍下马,高举黄绸包裹的圣旨:“陛下口谕:追赠王小仙为太师、尚书令,谥‘文正’,准建祠享祀,五司体制继续推行,三年后考评定夺!另谕:其子王元朗擢升翰林院编修,参预新政研讨。”
全场寂静片刻,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有人跪地叩首,有人相拥而泣,更多人转向那块无字碑,齐声喊道:“请立碑文!!请立碑文!!”
苏辙望着远方初升的朝阳,缓缓摇头:“不必。先生一生不爱虚名,这碑若刻字,反倒俗了。让它空着吧??空碑自有万人心填满。”
数日后,审计使抵达统万城。为首者乃户部郎中赵?,素有“铁面”之称,旧党亲信。他带吏员数十人,进驻政务厅,查封账册,传唤官吏,气势汹汹,似欲一举翻案。
然而当他翻开第一本《阳光账册》,眉头便皱了起来。每一笔支出皆有三方签押:经办人、监督员、百姓代表。粮米去向精确到村,水泥用量细化到方,连一张纸、一根钉都有记录。更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账册均公开张贴于市集公告栏,百姓可随时查阅质疑。
赵?连查三日,竟找不出半点纰漏。第四日,他微服私访市井,听茶馆说书人讲《王大人断案记》,其中一段说道:“某日有豪强谎报田亩,欲逃赋税。王大人命人取来‘鱼鳞册’与航测图一对,差了十七亩三分。当场杖责八十,追缴三年欠税。豪强嚎哭求饶,王大人只说一句话:‘天在上看,我在下查,你瞒得了人,瞒不了数。’”
周围听众拍案叫好。赵?默默饮尽一碗粗茶,悄然离去。
第五日,他召集随行官员,沉声道:“此地政务之清明,制度之严密,远超京师。我们若强行干预,非但拿不到罪证,反会激起民变。不如如实上报,言明此制可行。”
当晚,他亲笔撰写奏章:“臣历察诸路,未见如河朔之治者。官不敢贪,因账目公开;民不愿乱,因诉求有门。王小仙虽逝,其政不衰,其信犹存。所谓‘专权’,实为众治;所谓‘割据’,恰是共理。若天下皆效此法,何愁国不富、兵不强?”
与此同时,伊克昭草原深处,第一批“火种少年”已抵达目的地。他们在牧民营地支起帐篷,挂上手绘的《权利清单》布幡,开始授课。语言不通,便用手势比划;没有课本,就用炭条在地上写字。一个蒙古族孩子学会第一句话是:“我的牛被官抢了?去找监察司!”
黄河渡口,另一批少年联合艄公组建“水上议事会”,调解船资纠纷,制定航行规则。他们带来的《实录》被译成西夏文、回鹘文,在商旅间秘密流传。
西域商道上,一名十六岁少女主持的“女子学堂”开课第一天,便有三十多名妇女前来听讲。她们第一次听说“女子也可参议赋税”,激动得泪流满面。
而在汴京,王元朗每日清晨必赴国子监藏书阁,将父亲的奏章反复研读。他不再只是背诵经义的优等生,而是开始质疑律法中的不合理条款。一次廷议上,宰相司马光谈及“恢复祖制”,他竟起身反驳:“祖制若真好,何以百姓饿殍遍野?我父所行,非叛祖宗,乃是救苍生!”
满堂哗然。司马光怒斥其“狂悖”。但他毫不退缩,只淡淡道:“请诸公去西北走一遭,看看那里的渠、那里的学、那里的账本,再来论是非。”
赵顼得知此事,沉默良久,终叹曰:“王卿有子如此,可谓后继有人。”
春分过后,统万城迎来第一场暖雨。北岭渠水位上涨,灌溉系统全面启动。农民引水入田,麦苗破土而出,绿意蔓延如毯。
苏辙独自来到渠首石台,打开一只木箱??里面是王小仙生前用过的乌木杖、褪色紫袍、残破笔记。他轻轻抚摸那根磨得发亮的杖头,忽然发现内侧刻着极小的一行字:“宁负己身,不负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