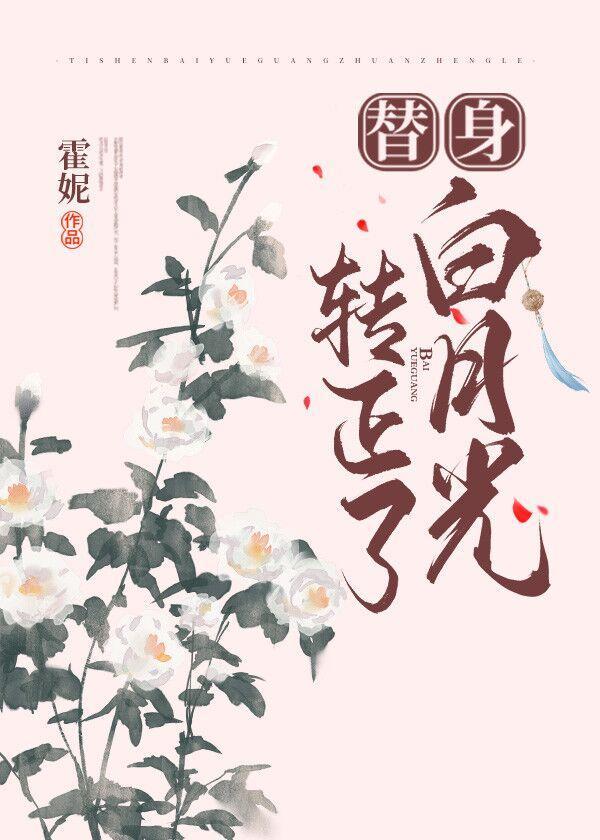02小说网>子不类父?爱你老爹,玄武门见! > 第二百四十七章 献子(第3页)
第二百四十七章 献子(第3页)
一声巨响,镜面龟裂,却不破碎。裂缝中流出金色液体,落地成字:
>“知伪而不避,方谓真。”
刹那间,整个空间崩塌重组。星辰坠落,化为书简铺满大地。一座全新的石殿拔地而起,比第九窟更加恢弘。殿门上方,赫然写着两个古篆:
>**第十窟**
门自动开启。内无珍宝,无机关,只有一张石桌,桌上放着一支笔、一瓶墨、一页空白竹纸。
墙上刻着最后一句话:
>“自此以往,不再有守护者,只有书写者。
>真相不死,因其永在重写之中。”
子墨跪倒在地,泪流满面。
他终于明白:所谓“第十窟”,并非实体,也不是传承体系,而是一种觉悟??**真理不能被保存,只能被不断重新创造**。昨天的“真”,可能是明天的“伪”;今日的“矩”,或许正是明日需要打破的枷锁。
真正的“持矩者”,不是固守旧规之人,而是敢于在关键时刻质疑自己、修正自己、甚至否定自己的人。
他颤抖着手,提起笔,蘸墨,在竹纸上写下第一行字:
>“余尝以为矩为不变之道,今乃知矩者,乃心中常省之刃。每念及此,汗出沾背,不敢自安……”
门外,李昭守候整夜。
天亮时,子墨走出石殿,双眼依旧失明,神情却前所未有的清明。
“找到了?”
“找到了。”他轻声说,“但也失去了。”
“失去什么?”
“那种以为自己一定正确的安全感。”
李昭愣住,随即大笑,笑声惊起飞鸟无数。
数日后,他们离开龟兹。临行前,那位比丘尼悄然现身,递来一只布包。
“这是阿罗檀最后的手稿残页,我一直藏着,等的就是今天。”
子墨触摸布包,里面是一小块织锦,绣着奇异图案:一只眼睛睁开,另一只闭合,中间交叉着矩尺与火焰。
“她说,真正的平衡,不在消灭火,也不在熄灭火,而在让火照亮矩,也让矩约束火。”
回到敦煌,子墨召集所有寻矩使,在书院广场宣读新定《寻矩律》十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凡持令者,每年须公开自省一次,陈述过去一年中最接近堕落的时刻,以及如何幸免。”
李昭听罢,叹道:“这比死还难。”
“正因如此,才有效。”子墨微笑,“防伪之道,始于承认自己也可能为伪。”
多年以后,当新一代寻矩使奔赴西南蛮地调查赋税暴政时,在一座荒村古庙中发现一幅壁画:盲眼老者坐于石台,膝上铜铃发光,周围环绕九道光影,分别代表九大守护世家的亡魂。壁画角落,一行小字:
>“心矩所向,即是光明。
>光之所至,火亦为薪。
>薪尽火传,代代不绝。”
而在长安皇宫深处,一位年轻宦官默默拓下这段文字,藏入袖中。他抬头望向御座??新帝年幼,权臣当道,谶纬再兴,民间已有“天命改易”之谣。
他低声自语:“下一个他,该出现了。”
风穿廊过,檐角铜铃轻响,一如当年。
远方葱岭,雪峰巍峨。
书院灯火彻夜不灭。
有人正在写下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