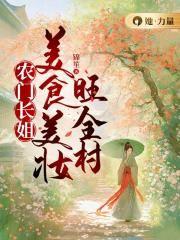02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131章(第2页)
第131章(第2页)
李思华放眼望去,铁路的两边,各有三道曲线防风堤,每道防风堤,并不是连续的,而是走一段、断一截,断的一截,又被别的防风堤补位,就像是“分段掩护”一样,有点军事掩体的味道。每道防风堤,基本都是坡型,高坡在向着铁路一侧,高度可达近4米,这样狂风吹上防风堤,就被引流向上吹,让铁路犹如处于一个空出来的“空沟”之中。三道防风堤彼此的错开,则让气流彼此在空中力量抵消。
铁路也不是直直的向前,而是选择大半径曲线,最小曲线半径不小于2200米,以提高列车的抗风能力和运行速度。
防风堤高坡的背侧,已经种上了一些抗旱的新疆杨。李思华叹息了一声,条件太艰苦了,希望这些树,能够活下来。未来在这里坚守的铁路国企员工,必然是全国最艰苦的条件。她提醒陪同视察的全国铁路总公司领导,未来这里的机务段,要修好宿舍等生活设施,在这里坚持的员工,必须实施特殊工资政策,比正常地区的要翻倍,其它地区不服气的,可以自己申请来这里,挣这个辛苦钱。
这里的修筑,铁路的进度是跟着防风堤的,由于加大了人力和机械投入,速度正在不断提升,已经修了近百公里了,再有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全线打通。
李思华一边听着铁总领导的汇报,一边心里寻思着。她明显感到,前世那个“基建狂魔”的初级形态开始形成了,此时新中国的基建力量正在迅速成长——毕竟从1934年到1939年,充足资本之下的5年大西南和大西北建设的训练,使得基建能力的成长很快,现在相对于前世,也就是规模还不能一下子扩大到那种庞大的程度而已。
但是抢了宝贵的时间——以铁路为例,现在修铁路的技术能力,大致应该与原时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以相提并论。原时空由于缺乏资本和机械,到七十年代,仍然是人力为主。
在新时空,铁路建设有了“三件神器”,使得新中国铁路的起始建设和质量水平,都远远超过了原时空建国前二十年。
第一件,是混凝土轨枕。此前旧中国一直是用优质木材作为轨枕,这太耗木材了,而且强度很难保持同一标准。而早在1935年,西华建总已经掌握了此项技术,现在早已经实现大规模普及,已经能够生产各种类型的混凝土轨枕(含岔枕、桥枕、宽枕、和专用线轨枕等)。
第二件,是龙门吊自行铺轨机。此时自然不可能做到后世的自动铺轨机。但是用柴油机做动力的铺轨机可以在铁轨上行驶,到断头的地方用龙门吊一根根地铺上轨枕,这自然比传统的让几条壮汉挑起轨枕,再一根根地放到位,要节省无数人力,也大大加快了速度。
第三件,是电传动大马力内燃机车+废气涡轮增压系统。在此前的美国工业引进中,1934年就引进了1000千瓦单节机车多节连挂的干线客运内燃机车,比较特殊的是废气涡轮增压系统,这是李思华在美国时就投资参与的科研项目,这也是她作为穿越者的福利,她记得是因为这个系统可以让内燃机车这样的动力系统增加功率50%以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铁路,乃至是火车,都是一个很高的起点。例如火车速度,平原直接达到了120公里小时,最高可达140公里小时,即使是在兰新铁路这样的大风区,也可以保持约100公里小时的时速。速度就是效率和运力,自然具备极大的战略意义。
现在以内燃机车为主的铁路运输,到1955年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即15年左右的时间后,将要改造成以电力机车为主。而再有15年,即1970年后,就一定要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李思华心里暗暗地寻思。
在视察兰新铁路之前,她已经看过了新京广线和宝成铁路,2条铁路都能保证在1940年竣工,这些视察,使得她对新中国的铁路修筑能力充满了信心。
在这两年修筑4万公里铁路后,她计划在1941~1945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再修筑10万公里铁路,使得新中国到1945年底,开通铁路达到17万公里,超过她前世穿越前中国的规模,当然科技水平是万万达不到的。
这并不是狂想,按照她的预计,由于开国之初,吃饭财政和养老财政的比例较小,因此财政比例中可以用于建设的比例较高,而且建设重点不同。她计划一五期间,每年保证1。2%的GDP用于铁路交通建设,这意味着5年时间将有1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铁路投资规模,按照1000公里1亿人民币(有一定市场化,但整体还是价格扭曲的,价格上升更多的是因为建筑难度)成本,那就是10万公里铁路。
在她原时空,只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两年达到了GDP1。2%的铁路投资强度,大多数时候,是在0。5%~0。7%,自然远远比不上新时空的条件。原时空的铁路建设,除了建国初期提升到了5万多公里以后,再一次大扩张的时代,几乎已经是二十一世纪,那是个完全市场化而且各项成本都极高的时代,自然不可能重演美国铁路当年狂飙猛进,一年修2万公里铁路的故事,但李思华在新时空,却可以做到。
李思华自己估算了一下,她前世修高铁,成本已经大致是1亿元只能修1公里,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修普通电气化铁路,大约也要1500到2000万修1公里。在新时空,此时币值对于未来物价,估计是1:100以上的比值,现在10万元修1公里,相当于原时空1000多万修1公里,很合算的价格,总体还是低价区,此时不大修,未来一定会后悔。
想到财政,她不由得幽幽一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虽然有很大的一笔收入,但那是一次性的,常规的长期投资,才是当家人痛苦的事情。
按GDP来分,铁路1。2%,公路、机场和其它交通1。3%,这就是2。5%。教育3%,科技1。5%,城乡建设2%,农林水利2%,军事军工6%,医卫文社等其它1%,这就是18%,财政收入总共约为20%左右,国家只剩下2%作为吃饭财政,哪里够啊?要不是有那笔大额一次性收入,大概现在就要开始发行国债了。
幸好现在中国人普遍年轻,没什么养老压力,要不然,单单看财政,让她上吊的心都有。
还好从1941年开始,国家财政会逐步提升税收,逐渐增加到25%,最后会达到30%左右,这样才能支撑起大国的正常发展,她心里不由得念叨着。
除了铁路,当然还有公路,同样要利用处于“低价时间”的优势,加快建筑,一五期间,干线公路的建设规模会超过60万公里,到1945年底使得新中国干线公路(即国道,大致相当于原时空的二级公路左右的水平)的总规模,达到75万公里左右,基本形成全国的公路干线网。
至于高速道路,她现在还不敢想,成本太高了,先用国道干线,解决有无问题,未来实力强了,才是优质道路的问题。
铁路和干线公路(国道)是主动脉和动脉,城乡公路和乡村公路则是支脉和毛细血管,一样都少不得,但资本永远都不够,生产能力暂时也不够,她也只能按捺下她心头隐隐的焦灼,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不得乱不得。
重庆半岛的最高处鹅岭,李思华纵目远眺两江(长江、嘉陵江),江对岸灯火璀璨,这座中央直辖的大城市正在迅速地“现代化”发展中。
在以内循环为重心的新中国经济地理布局中,重庆自然是几个重点城市之一。这里是长江上游唯一的真正全年通航港,又是四川盆地乃至整个西南向东的门户,所谓“四川”,其实在重庆体现得最明显——沿嘉陵江往上可至川东北重镇南充,循涪江而上可至川北第一市绵阳,溯长江岷江而上可至川中名邑乐山,由沱江而上可至川南锁钥泸州。总之由重庆沿此四条大江,可以制控和辐射整个四川,再发散到整个西南。
所以水路交通的便利,是重庆这座山城立足的根基和之所以在历史上兴起的前提,四川多山,水路交通的重要性因此尤为突出。重庆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如果不是水路的便捷,这里是难以崛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
李思华想着,尤其是目前重庆市的核心渝州半岛,这里地势险峻,地形起伏崎岖,沟壑纵横,在古代军事地理上易守难攻,所以历史上是因为南宋抵抗蒙古侵略,修筑大型山寨型城市而形成,古老的底子是一个大型军寨。如果不是古代军事上的需求,重庆肯定还会在,但也许其市中心,就会略微偏移到不那么崎岖的地方。
渝州半岛这样狭窄的地形,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是不宜于抵御空中打击的,人口太过密集。她想起前世渝州半岛这里市中心,密密麻麻的高架、轻轨、桥梁和超级复杂的道路系统,不由得头皮有点发麻,还是必须进行一定的分散。
重庆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总的地势是东南部、东北部高,中部和西部低,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总体来看,两江隔断的各个地区实际都属于小丘陵,地形并没有想象的山区那样难以建设,按照前世的“一小时经济圈”进行划定,其中心建设区域(面积超过2万平方公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平地或者高低差在几米、十几米左右的小山坡,属于丘陵地形,而且实际上近郊已经有着稠密的小镇和道路网络,基础条件并不差。
这就很适合发展“组团式城市”,这正好符合李思华“分布式节点城区”构成大城市的理念——每个城区之间应有一定的绿植和乡寨进行区隔,用道路、桥梁和轻轨进行城区之间的连接,总之,是不能把鸡蛋都放在渝州半岛市中心这里。
在重庆进行城市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里的地基硬、地质好,地下直接就是岩石,根本不用打很深的地基就能修建高层建筑,这相比上海那种软豆腐地基,在建筑上要节省不少钱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