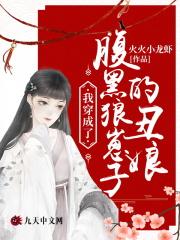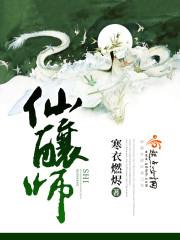02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139章(第1页)
第139章(第1页)
“新中国需要的,就是“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华文明、中国国情和底层人民发展需求这三大基础上,构建的新经济学。对于国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说白了,那些都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确实有一定参考的价值、研究比较的价值,但我们要小心地把糖衣剥下来,而将毒药丢弃,切不可不假思索地盲目引进和应用。”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首先要实现的,是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中国本土的经济实践,给予解释和指导,而不是什么“贡献于世界”。自己还没有走稳呢,奢谈什么贡献世界?”
“中国经济学,必然采纳马恩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不是完全遵循和教条地尊崇,马恩是在欧洲生活,从未到过中国,而且他们的理论是七八十年前的了,其太多的“假定”,与今天我们经济面临的环境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扬弃”,我们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立场,而不是具体的经济理论和手段。例如中国经济学,不会去涵盖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经济发展,因为两国的文明、国情甚至底层人民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前提都完全不同,很多经济理论自然也不一样。”
李思华最后总结,我们既不能“言必称希腊”,也不能“言必称苏联”,中国就是中国,自有自己的文明、国情和人民特征,只能是“唯中国经济学”,希望各位学者从这样的角度,努力研究,为国家民族,提出有实用价值和有指导意义的新经济理论。
李思华的讲话对经济学家们震动非常大,她提出的完全是一个总原则,未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必然要求遵循这个总原则来形成,自身的经济研究能否被承认,显然是必须符合这个总原则的要求的。
有几个经济学家脸色惨白,他们明白,自己以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为核心的“学术道路”完全被否定了,未来西方经济理论,只会是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种“参考”,而不会是主流。
李思华的一个计划,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
她说明,最近几年她在忙碌之余,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初探》的书,准备作为大学经济学的主要教材之一。这让在座的经济学家们精神都一震,他们迫切想读到这本书。
李思华坦言“我自己都不认为自己这本书的理论、思想、逻辑和观点,肯定是一定正确的,所以在每个章节背后,我计划要附上很多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也有可能是赞同的,但不管赞同还是反对,每一种观点都要求言之成理,有着自己的逻辑,甚至有着实证案例。”
“这个方式,就是提供学生全方面的思考,而不是填鸭式的接受,让他们知道,每一种经济理论可能都有适用性、或者谬误性,接受之中,必须始终保持着怀疑,我们要的,就是人人成龙,要一些温顺的羊群的话,是想干什么呢?”
“这个大工程,自然需要很多经济学家来完成,我希望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多一些,共产党人不害怕错误,改正就行,害怕的就是粉饰掩饰,这会对未来的革命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
李思华的态度赢得了这些经济学家的好感,很多人觉得她“风光霁月”,不少人决定认真地参与这个工程,她的这本书,可能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自己参与完善,也是留名青史、影响国运的大事件,这比自己发表十篇八篇论文,重要得多。
话题很快转向了新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李思华称之为“半战时体制”,又称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的经济体系,将是“准军事化”的,这个论断,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冲击很大,不少人是反对战时体制过于延长的。
原厦门大学校长、《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者王亚楠就不太认可,他向李思华说道:“李总理,战时状态长期维持是不可行的,这会对国民经济的平衡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压制民用工业和产业的发展。”
李思华笑着解释:“包括您王校长在内,可能大家对我所说的半战时体制和准军事化的内涵有所误解,我来解释一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战时体制大家很熟悉,这是为了应付大规模战争而采取的临时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本质上是短期的。重点是在国民经济中向军事倾斜,优先将经济资源用于军事和战争准备。本质上,这是以高度集中的生产、分配和管理体制,来提高战备和军事准备的效率。”
“我们现在说半战时体制,就是因为当前的国际环境,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国家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倾斜到军事准备上,例如,这几年的军费比例,占到了财政支出的30%。这在和平时代本身是不正常的。但坦白地说,没有办法,当下所有的大国,除了美国还没有完全发动外,其它国家都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投入战争或者准备战争。我们能够做到不完全将所有资源投入战备,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点点头,他们也很清楚,这不是正常的时代。
李思华继续说道:“如果未来大战结束,各大国都开始裁军,我们自然也会将战备的规模降下来,将军费的比例降下来,解除现在这种半战时体制。”
“不过说道准军事化,其实可能对这个词有所误解,它与战时体制毫无关联。它指的主要是国家以军事化的一些模式,来进行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执行,其内涵有类似苏联斯大林模式以及日本德国的军国民化的一部分,但又在很多方面不相同。”
“回顾世界国家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后进国家往往会有一个阶段,在国家体制上实施一定的军事化,来推进国家的初步快速发展。例如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初期阶段,例如苏联建国后从战时体制到斯大林体制。”
李思华在这里不方便提到日本,其实日本也是得力于这种“军事化指挥”的国家体制的,二战后日本的复兴,除了其它各种条件,吉田茂政府的主要官员,就是当初日本918之后在我国东北殖民地的主要官员,而日本在东北实施的其实就是这种军事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批官员熟悉的就是这样的管理体制,即通过顶层设计,拟定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主要建设内容,然后集中政府和社会资源,强制发展,以此再带动私营投资。
二战后日本复兴,在经济体制上实际上得益的,就是这种后世被大批“经济学家”诟病的体制。李思华收回思路,继续说道: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建国或者改革的初期,民众的心气最高,奋斗意志最强,对困难和艰苦的承受度最高,这就使得军事化的管理最有效率,能够让指令得到比较彻底的贯彻。”
“为什么要军事化?因为人类组织起来的中心化管理组织中,军事组织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具备最高效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新中国目前的经济组织,有不少是准军事化的,例如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建设,例如不少大型综合工业基地的建设。而很显然,事实证明,在军事化的组织下,其建设效率甚至建设质量,都远远超过了任何市场化的组织。”
“所以准军事化,就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国家可以在短期内,按照顶层规划建立起良好的基础,而后来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良好发展。”
“本质上来说,建国初期犹如人大病初愈,想要马上按照市场化的规则来组织经济,将是缓慢的,这个时候普通经济措施的效果非常滞后,通过国家手段强行调配,反而是最快、最合理的方法。准军事化就是一剂良药、一剂补药,让人快速恢复正常的健康。”
“当然,是药三分毒,准军事化不是万能的,它讲求严格的纪律、精神奉献、降低生活享受。所谓刚不可久,在经过十年左右的阶段后,还是必须过渡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正常经济发展阶段。”
李思华的说法大大出乎了这些经济学者所料,虽然很多学者其实早已反复研究了新中国这两年的经济政策,但按照李思华现在所说,仍然感到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看得明明白白了。
李思华笑了笑,继续说道:“其实现在客观条件还不适合全面市场化,当然以后我们也不会实施全面市场化。现在的经济制度、管理体系、资源配给都不完善,放开市场化,任由市场漫卷,很可能并不能带来经济大发展,反而是少数人,就可能通过投机手段,急速垄断大量资源和财富,导致大多数人会无法生存,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
顾谆说道:“李总理不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地分配资源的手段吗?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市场,但我听说李总理曾经将之视为对幼稚儿童的烟雾弹。”
李思华点点头:“市场很重要,市场是最重要最珍稀的资源。但我反对将市场神话,市场调配资源的有效性,其前提是参与市场交易的各方,必须具有同等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可以进行平等的博弈。但在现实中,这种条件根本不存在,所以市场一定是必须有所管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