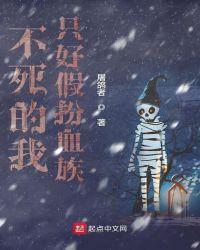02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169章(第1页)
第169章(第1页)
上了专车,李思华呵呵一笑,中美两国的友谊?能保持10年就阿弥陀佛了,大争之世,外交语言终究只是外交语言。
专车开进奥斯汀的时候,李思华才发现她远远低估了德州人对她来访的狂热。道路两旁站满了人,很多人还挥舞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很多人在专车经过的时候热情地呼喊,她只能隔着车窗向他们挥手致意。她还不知道,今天美国绝大多数媒体上,李思华访美的新闻都是头条,大量的“女皇归来!”、“红色女皇重临德州”、“今天,德州恭迎女皇的驾临!”之类的标题满天飞。
在中美还没有交恶的这个时代,德州人是以李思华为骄傲的,她是德州人对东部人称他们为乡巴佬的一种反击。李思华在德州成为全球女性第一富豪,然后居然回到中国领导革命,成为这个6亿多人口、领土1600多万平方公里的全球最大的国家之一的两位领袖之一。这样的传奇人生,让德州人平时就津津乐道,李思华的5年德州生涯,让德州人觉得李思华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自然对她的成就与有荣焉。
实际上,在后来中美关系恶化后,美国媒体将李思华形容为“红色巫婆”的时候,很多德州人仍然对她充满好感,美国记者都知道,在德州说李思华的坏话,很难得到欢迎,说不定还会得到德州人的老拳。
专车缓缓行驶到德州州府的门口,李思华下车,就看到麦基逊等人等候着她,德州财团的5大家族的家主,一个不拉,全部都在场。
这几个家族此时是非常感激李思华的,单单中国将达拉斯第一国民银行,指定为中国自贸区国企对美贸易的结算和汇兑银行这一个动作,就轰动了美国财经界,让这家银行的股票,上涨了近5倍,而这家银行以麦基逊家族为主,但其它4个家族都持有大量股份,因此如此的暴涨,让他们的财富都大大增值,怎么可能不感谢李思华呢?
当然,这是当下的好处导致的,未来中美交恶后,他们就要避嫌了,这对他们无所谓,资本家吗,以利益而交,因利益而散。
李思华微笑着上前,与麦基逊等握手,德州的州长在一边鼓掌。等到李思华与几位家主们寒暄后,他才走上前与李思华握手,欢迎她“回到”德州。
李思华在德州,主要是洽谈了一些经贸合作,例如德州石油出口中国,与德州的农业合作等方面,也包括中国服装和轻工业品出口德州的相关内容。她还将原来安华在德州的几十个工业技术学校等建筑,捐给了德州政府,用来“作为福利救济等慈善用途”,再刷了一波美国人的好感。反正这些学校早在1946年就已经全部结束,美国不可能再让中国,如此地利用美国技术人员和企业进行工业人才培训。
在德州之后,她又飞临加州,同样在加州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不过在加州,就发生了一件让所有美国人都觉得尴尬的事情。加州最著名的是两所大学,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李思华参观了加州大学,但是拒绝了参观斯坦福大学,并且当着一众记者的面,痛批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斯坦福夫妇,她向记者们陈述了斯坦福大学的历史,直言这所大学,是建筑在被拖欠工资又被屠杀活埋的华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看到听到“斯坦福”这个名字,都让她觉得恶心,这就是一对魔鬼夫妇,是美国的耻辱。她还反问记者,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真的以斯坦福这个名字为傲?他们不觉得恶心吗?
这件事震撼了美国,而记者们自己去寻找证据的时候,发现李思华的陈述完全是真实的,这就尴尬了。斯坦福大学当局觉得“锅从天外来”,用了各种方法辩解,但是这有什么用呢?摆明了就是声望大跌,使得很多美国学生不再考虑入读斯坦福,因为他们觉得未来终生,这都会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而中国现在斯坦福是没有留学生的,美国开放后也不允许入读此校。
甚至少数来自爪哇民国的华人留学生,都觉得压力山大,那个时代的爪哇民国,不像原时空的台湾,至少还是讲究民族主义的,毕业于斯坦福的话,在他们想来恐怕会变成一辈子的污点,于是绝大多数最后都转学了。
这件事让斯坦福大学元气大伤,虽然美国种族主义盛行,但这件事不符合所有的政治正确,实在是无法洗白,2年后斯坦福大学只好更名为湾区大学,但美国人都知道这段历史,以至于即使是几十年后,一旦有人提到斯坦福或者湾区大学,还是有很多美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喔,是那所由一对魔鬼创立的学校。”因此几十年后,这所大学也没能彻底缓过气来。
当然,新时空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人就淡忘了这件事,何况那个时候中美的仇怨越来越深,自然反而有人为斯坦福夫妇叫好了。
1951年的1月,李思华在华盛顿,与杜鲁门和马歇尔举行了会谈。
李思华与杜鲁门,两人都对对方很好奇。杜鲁门对李思华的好奇很自然,世界上的政客,没有不对李思华这样的“奇葩”不感兴趣的,何况杜鲁门已经见识到了李思华的手段,她到达美国后,大谈中美友好,但在加州又用斯坦福的历史反刺一记,这算是“又打又拉”?软中带硬,很不好应付。
李思华对杜鲁门的好奇,则是她一直认为,杜鲁门在历任美国总统中,虽然比不上罗斯福和埃森豪威尔,但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政治上很高明,将美国在二战的军事胜利,彻底地转化成了美国的霸权,奠定了美国此后数十年西方霸权首脑的稳固地位。不过他在经济上的作为,乏善可陈,远远比不上开创了美国高速公路网的艾森豪威尔。
和杜鲁门的谈判,是比较轻松的,李思华早知道杜鲁门虽然反共的意识形态强烈,但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讨厌犹太人,却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家;他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一度欲参加3K党,却邀请黑人出席他总统就职典礼的招待会和舞会,发展了美国的民权;他坚决反苏,但同时坚决避免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
马歇尔也是个现实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谈判,就易于实现,因为双方都没有过多的奢望,都是着眼于长远。因此谈判很顺利,实际上马歇尔访华的时候已经基本都铺垫好,只是以两国正式公报的形式,确定下来。
几天后,中美公报发布,全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将在沿海打造两条“自由贸易之弧”,美国会对等开放两州作为对华贸易区等等。
中美关系的正式正常化,使得中国打开了与西方所有国家的正常外交,包括关系一直非常僵的戴高乐法国,也不得不与中国建交,中国没有向法国追讨庚子赔款,因为中国拿回了安南、柬埔寨和老挝这3个法国殖民地,充分地报了仇。
第267章右派集结号与资本僭越
1951年的4月,李思华阅读着报纸,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冷笑,心想该来的总是要来。
她读的文章,正是沪苏市某党报的一篇社论。文章从李思华访美出发,欢呼中美之间走向正常化,文章的前半部分挑不出太多的毛病,你最多说他对于美国过于幻想和天真。但是后半部分笔锋一转,谈到目前国家政策上对私有企业诸多限制,严重束缚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因为他们的所得相对于贡献,对比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严重不足的,这导致他们对于扩大再生产顾虑重重,也不利于在今后的自由贸易区内,与美国等西方企业竞争云云,总之是呼吁国家应有一定的改革。
这很正常,李思华内心平静如水。建国已经12年了,豪不客气地说,从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来看,比得上前世的40年,大致应该已经相当于原时空的1990年左右的生活水平。
经济发展了,私有经济也壮大了,总有些人不甘寂寞,而干部群体中也有一些人,在长期的和平生活中迷失了革命的理想。在一定的小范围内,就会出现私有资本,与与舆论、知识和权力的合谋,试图推动国家向他们期望的符合他们小团体利益的方向走。
李思华知道,在她前世,学术上有一个著名的“格瓦拉困境”的“革命魔咒”理论,这个理论以拉美的著名革命者格瓦拉命名,因为格瓦拉的一生正好代表了这个理论的典范。他是一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努力方向确定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进入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他牺牲在自己的理想中。
格瓦拉困境表明:很多革命者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价判断,皆集中于革命活动,革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离开了革命,激情就不再燃烧,精神走向虚无,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原时空后来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走向消亡,国际共运式微,很多专家认为与格瓦拉困境很有关系。
屠龙者成功屠龙后,要么自己变成恶龙,而不想变成恶龙的人,很多变得茫然无措。中共在原时空后来曾经说过要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是对是错?
这曾经也是李思华的困惑之一,她曾经与毛泽东多次探讨这个问题。最后两人达成一致的看法是,格瓦拉困境其实是陷入了“路径依赖”,革命的路径本来就不是唯一的,必须要根据环境而变,建国后基本进入了和平和建设的时代,与此前战争与牺牲的时代不同,革命的方式、模式肯定要发生变化,唯一不能变的是革命的思想和初心。
原时空有句口号说得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的初心是什么?是解放无产阶级,带领他们去奋斗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手段是什么?建国前的手段是战争,用暴力来消灭剥削食利阶层。建国后的手段是什么?是建设和守护,驱动底层人民投入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守护人民的胜利和奋斗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