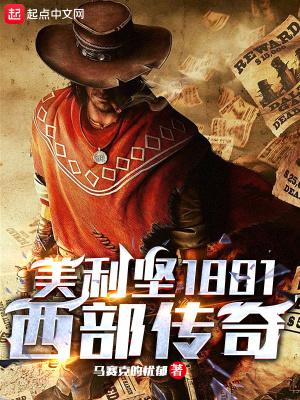02小说网>无用之神谋天下 > 寻人画像(第2页)
寻人画像(第2页)
丞相沈巍端坐主位,面容清癯,眉宇间是挥之不去的忧色与疲惫。四个月了,爱女音讯全无,如同人间蒸发。夫人王氏更是以泪洗面,缠绵病榻。府中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方才门外的喧嚣隐约传来,管家沈忠匆匆进来,低声禀报:“相爷,门外又来了个泼皮,声称在清河镇悦来客栈见到了小姐……”
沈巍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摆摆手,连话都懒得说。又是这种消息……起初他还抱着一线希望,亲自过问,甚至派人去核实过几次,结果不是认错了人,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白白耗费心力,徒增失望。次数多了,连沈忠都不再详细禀报,只简单提一句便打发了。希望一次次燃起又熄灭,那种煎熬,比绝望更甚。
“罢了,让门房仔细些,莫再让这等闲人搅扰夫人清净。”沈巍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倦意。
“是。”沈忠躬身退下。
然而,沈巍毕竟是历经宦海沉浮的一朝宰辅。失望归失望,一丝属于父亲的本能,或者说一种近乎偏执的不甘,仍在心底最深处挣扎。他闭上眼,眼前浮现出女儿熙然巧笑倩兮的模样。万一呢?万一这次是真的呢?清河镇……离京不远……悦来客栈……
“沈忠!”他猛地睁开眼,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迫。
刚走到门口的沈忠连忙转身:“相爷?”
沈巍站起身,在厅中踱了两步,最终下定决心:“……你亲自带一队府卫,快马去一趟清河镇的悦来客栈。不必声张,暗中查探一番。若……若真有什么‘极贵气的大人’带着女眷入住,务必仔细辨认,速速回报!”
“是!老奴这就去办!”沈忠心中一凛,立刻领命而去。相爷终究还是放不下那一丝渺茫的希望。
夜色如墨,沈忠带着十余名精干府卫,策马疾驰出城,为赶时间,走了小道,马蹄踏碎寂静,直奔百里之外清河镇。
当他们风尘仆仆、满身寒露地抵达悦来客栈时,已是第二日黎明破晓时分。客栈刚刚开门,伙计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
“店家,昨日可有一位气度不凡的大人,带着一位年轻姑娘,在此投宿?”沈忠急切地问道。
掌柜的见这阵仗,吓了一跳,连忙回忆:“回这位爷的话,昨日傍晚是来了一队贵客,领头的公子爷瞧着就尊贵得很,带着不少护卫,是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同行,住在天字号上房……不过……”
“不过什么?”沈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不过他们天不亮就结账离开了,算算时辰,走了得快半个时辰了。”掌柜的答道。
“走了?!”沈忠如遭雷击,一股巨大的失落感瞬间攫住了他。他冲上楼,直奔天字号房,推开门,只见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床铺整齐,仿佛从未有人住过,只余一丝若有若无的清冽冷香在空气中飘散。
沈忠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望着窗外渐渐亮起的天光,一股难以言喻的懊恼和愤怒涌上心头。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他猛地一拳砸在门框上,木屑纷飞。
“追!”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带着不甘的嘶哑,“立刻给我追!往盛京方向!务必探明那队人马的身份和去向!”
府卫们轰然应诺,再次翻身上马,沿着官道疾驰而去。然而,谢临煊的队伍皆是精锐,又提前出发了半个时辰,岂是那么容易追上的?沈忠的希望,如同晨曦下的露珠,在追赶中一点点蒸发殆尽。
另一边,通往盛京的官道上。
玄黑马车平稳行驶。车厢内暖意融融,谢临煊闭目养神,仿佛对昨夜客栈可能发生的风波一无所知。
苏沐童则掀开车帘一角,好奇地打量着越来越近的盛京轮廓。那巍峨的城墙,高耸的城楼,鳞次栉比的屋宇,无不彰显着帝都的恢弘气度。一种奇异的、既陌生又仿佛带着一丝遥远熟悉感的心绪萦绕着她。她看着看着,忽然没来由地打了个喷嚏。
“怎么了?”谢临煊睁开眼,目光落在她身上。
“没……没什么,”苏沐童揉了揉鼻子,放下车帘,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许是昨夜没睡好,或是……嗯,感觉好像有人在背后念叨我似的。”她随口开着玩笑,并未放在心上。
谢临煊深邃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一瞬,那眼神复杂难辨,似有深意,又仿佛只是寻常的关切。他并未接话,只淡淡吩咐车外:“加快些速度,巳时前进城。”
马车微微加速,将清河镇的风波与丞相府的追寻,彻底抛在了身后扬起的尘土之中。身份的秘密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虽暂时未激起惊涛骇浪,但那扩散的涟漪,却已悄然改变了水下的流向。盛京,这座汇聚了天下权势与风云的城池,正张开怀抱,等待着“谢沐童”的到来,也等待着“沈熙然”真相的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