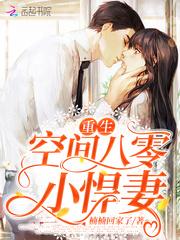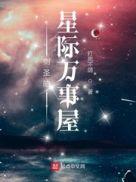02小说网>重生1991:春潮晚来急 > 第196章 清代雍正御窑(第1页)
第196章 清代雍正御窑(第1页)
虽然她很擅长“拼图”,但却是第一次这样备受瞩目,为了待会修复时不出差错,她找研究员要来纸笔,低头伏案,认真画起了图。
时应染跟她差不多,不过他画图的习惯跟时天华一脉相承,不但要画整体图,还要画出正、反、上、下四个角度的图。
十几分钟过去,两人分别都画好了图,周围的人对比了一下,发现它们的图案相似,器型却略有区别,这正契合了之前贺知风的说法。
不过最后修复出来的实物是不是和他们画的图一样,还不知道。
但大家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紧紧地汇聚在他们的手上。
时应染现场要来材料,调和了一种胶,有速干地功效,能够暂时把瓷片暂粘连起来,进行定形,只是不能保持太长的时间。
张副馆长一边看他的动作,一边点头,“这是咱们常用的粘连剂,没想到阿染早就学会了。”
时天华不由得想起他第一次制作这种粘连剂时的模样。
那时的时应染才十来岁,为了争一口气,让他看得起自己,周末把自己关在房里做实验,反复倒弄那些化学试剂。
有一次还差点烧伤了手,要不是汪月梅发现,狠狠把他批了一顿,他还不知道自己无意中脱口而出的一些话,对时应染居然会有那么大的刺激。
这时,时应染已经把瓷片一块接一块地拿起来,行云流水般在它们的边缘抹上胶,把它们一块块地粘在一起
。
很快,梅瓶的底部成了形,接着是腹部,雪花般的瓷片不断地网上粘,一只梅瓶就像是从无到有般生长了出来。
至于贺知风,也亲手调配了一种粘合剂,粘稠程度看起来比时应染的要大,但也因为如此,她涂抹的速度比时应染要慢,时印染已经拼到腹部时,她才拼完足底。
本来以他们的功夫,把这两只瓷片完美复原不成问题,但因为年代久远,有些碎片缺失,所以只能复原个百分之八九十,但即使如此,整个梅瓶的器型和主要图案都能显现出来。
由于是出土瓷片,有些太过细小的碎片隐没在泥土里,无法收集起来,以致于有些裂痕比较明显,只能依靠后期的增色修复。
不过目前为止,贺知风和时应染已经完成了初步修复的过程。
他们拼齐了碎片,把每一块都放在了它该放的位置,且没有任何错漏。
“好!真是太好了!”张副馆长忍不住叫了声好,兴奋得面色红润。
时天华也欣慰非常,忍了忍实在没有忍住,上前拍了拍时应染的背脊,就算是表扬了。
时恩赐神色莫测地看着他们,心中的忧愤依然没有减轻。
不过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在注意他,大家都挤在一起,查看这两只被临时修复的梅瓶。
“胶水维持不了多久,不如先拍照吧。”时应染提醒道。
“对对,先拍照!”一位研究员立刻应和道,从办公室拿来照相机,劈里啪
啦各种角度都拍了个遍。
他们修复瓷器时,也经常会这样,先把完整的器型复原,拍照存档,再商量选择什么材料,什么手法来修复瓷瓶,以确保能尽可能地呈现出它原本的模样。
而此时,先前无法看到的瓶身线条,完全映入所有人的眼帘,贺知风修复的这个梅瓶下半身确实略粗,肩颈的过度也不太自然,比起明代瓷瓶,更为符合清代梅瓶的特征。
不需要旁人说什么,时恩赐已经不自觉吸了一口凉气,胸口钝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