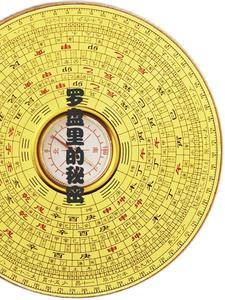02小说网>黄昏之下(校园双强) > 第五十二章 逃避(第1页)
第五十二章 逃避(第1页)
陆燃没有动。她就那样静静地站在病房门口,隔着几步远的距离,目光一瞬不瞬地落在那个倚靠在床头、怀抱铁盒的侧影上。
羽绒服还没来得及脱去,肩头还带着外面夜风的寒意。她不想惊扰她,哪怕只是细微的声响或动作。
她像一株在寒夜里悄然生长的植物,固执地、沉默地,将所有的担忧、心疼和跋涉而来的风尘,都收敛进安静的凝视里。
时间在消毒水的气味和仪器规律的滴答声中缓慢流逝。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病房里的光线没有变化,窗外的夜色依旧深沉。
陆燃站得腿有些发麻,眼睛也因长时间专注而微微酸涩,但她依然没有移开视线,仿佛要将这分离数月后重逢的第一眼,刻进骨子里。
终于,或许是长时间被注视带来的微妙直觉,或许是窗外某束偶然掠过的车灯惊扰了沉思,病床上的人,极其缓慢地转过了头。
目光相撞的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
沈清嘉的眼睛猛地睁大,里面清晰地倒映出门口那个熟悉又似乎有些陌生的身影——陆燃。
她穿着深色的羽绒服,头发被北风吹得有些凌乱,脸上带着长途奔波后的疲惫,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亮得惊人,里面翻涌着沈清嘉无法承受的、太过滚烫和直白的情绪:
惊喜、心痛、焦急,还有几乎要溢出来的思念。
惊讶如同冰层下的第一道裂纹,瞬间爬满沈清嘉的心壁。
紧接着是恐惧——她怎么会在这里?妈妈!一定是陈颖!她又自作主张,又去打扰陆燃了!
这个认知带来一阵强烈的、被彻底背叛和无力掌控自己生活的愤怒。然后是更深切的、几乎将她淹没的不可置信和……难堪。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苍白,消瘦,虚弱,穿着丑陋的病号服,手腕上连着冰冷的输液管,像一个不堪一击的废物,被困在这间充斥着失败和脆弱的白色房间里。
这样的她,怎么能见陆燃?怎么配得上陆燃那依旧明亮、充满生命力的目光?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几乎是一种动物般的本能,在看清陆燃的那一刹那,沈清嘉猛地转回头,同时用尽全力,将自己整个缩进了被子里面!
白色的被褥迅速隆起一团,剧烈地颤抖着,将她完全遮盖,隔绝了视线,也隔绝了那个让她无地自容的世界。
逃避。这是她此刻唯一能做的,也是她认为必须做的。
我这个样子,怎么见你。
不,我不想看到你。
不想让你看到这样的我。
她在心里无声地嘶喊,牙齿紧紧咬住下唇,尝到一丝腥甜。被子里的黑暗和狭窄给了她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却也让她无处可逃地直面自己汹涌的羞耻和痛苦。
她依旧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用被子将自己裹得更紧,隔绝了光,也隔绝了空气,仿佛要将自己从这个令人绝望的现实里彻底抹去。
因为激烈的动作,她原本放在被子外、连着输液管的手猛地被牵扯。
留置针在皮肤下狠狠一扭,尖锐的刺痛传来,但她仿佛没有知觉,只是更紧地蜷缩。针头附近的胶布翘起,细细的输液管在空中危险地晃荡。
陆燃站在原地,心脏像被那只扯动输液管的手同时攥紧。她看着那团剧烈颤抖的被子,看着那晃动的输液管,脚步下意识往前挪了半步,又硬生生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