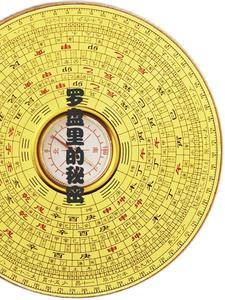02小说网>黄昏之下(校园双强) > 第五十二章 逃避(第3页)
第五十二章 逃避(第3页)
12月23日,陆燃,你现在在跑步吗?我想吃芒果干了。
12月24日,“陆燃,面包好硬,我好想吐。”
12月25日,陆燃,今天是圣诞节,你冷不冷?你妈妈有没有给你织毛衣?
12月26日,陆燃,外面的光好刺眼,我把窗帘拉上了,遮住太阳,也好像把你遮住了。
12月27日,陆燃,今天我去临潇河,想到你那天抱着我,也好想念倩倩的熊博士软糖。
12月28日,雾霾,陆燃,我的头好痛,我不知道怎么了,我睡不着。
不是连贯的叙述,而是碎片式的倾诉,压抑的笔触,越来越多的泪渍晕开了字迹,将那些“陆燃”、“想你”、“冷”、“睡不着”、“吃不下”反复浸润,模糊又清晰。
一次,两次,三次……看着自己的名字被一遍又一遍地写下,看着那些被泪水打湿又干涸的褶皱,陆燃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反复揉捏、撕扯,痛得她几乎无法呼吸,喉咙被巨大的酸涩堵住,视线迅速模糊。
沈清嘉,你为什么……任何事情都要自己扛?我们不是战友吗?不是说好了“有我在看”吗?
沈清嘉,你有这么多天,都没好好吃过一顿饭,睡过一个好觉了吗?
沈清嘉,我还没带你去天文馆,看真正的、完整的星空,你怎么就……倒下了?
沈清嘉……我也,很想你。
滚烫的泪水终于冲破眼眶,大颗大颗地砸在日记本粗糙的纸页上,和那些旧泪痕重叠、融合。她慌忙用手去擦,却越擦越湿。
她只能紧紧攥着日记本,将额头抵在冰冷的玻璃窗上,肩膀无法抑制地剧烈抖动,压抑的呜咽声从喉咙深处溢出,在空旷安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而破碎。
病房内,那团隆起的被子依旧在微微颤抖。沈清嘉将自己深埋在一片黑暗和潮湿之中,情绪像脱缰的野马,失控地奔腾。
豆大的泪珠不断滚落,很快在枕套上洇开一片深色的水迹。她死死咬住被角,不让自己哭出声,身体却因为极致的压抑和悲伤而抖个不停。
她为什么要来?是陈颖又去求她了吗?她是因为……想我才来的吗?还是仅仅因为同情,因为责任感,因为自己这副病恹恹的样子?
混乱的思绪、自我厌弃、对母亲擅自做主的愤怒、对见到陆燃的渴望与恐惧……种种情绪交织冲撞,让她本就昏沉疼痛的脑袋更加晕眩,像要炸开一般。
她恨不得自己立刻昏过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感受。可是她停不下来,整个人蜷缩在潮湿冰冷的被窝里,抖得像秋风中的最后一片落叶。
病房内外,一墙之隔,两个少女,一个在被子构筑的黑暗堡垒中无声崩溃,一个在走廊冰冷的窗前泪如雨下。
同样的悲伤,同样的思念,同样的无能为力,却隔着那扇门,无法传递,无法交融。
走廊长椅上,陈颖听着陆燃压抑的哭声,看着病房门缝下透出的、死寂般的光,再想起日记里女儿那些绝望的文字,终于彻底明白——自己从头到尾,或许都未曾真正了解过这个女孩身上那份真挚和热忱,也从未真正走进过自己女儿那个看似优秀完美、实则早已不堪重负的内心世界。
但是,一切都好像太晚了。她的女儿,已经被她自以为是的“爱”和“期望”,折磨得面目全非,缩在壳里,连见一眼想见的人都不敢。
为什么她当初没有发现女儿日渐消瘦下的沉默是求救?
为什么她要在生日那天,挥出那摧毁性的一巴掌?
为什么……
无边的悔恨,如同冰冷的潮水,在这个寒冷的跨年之夜,将她彻底吞没。